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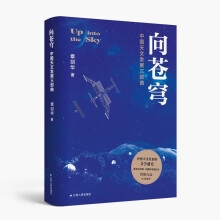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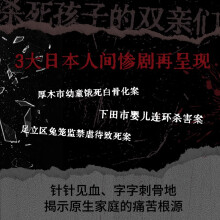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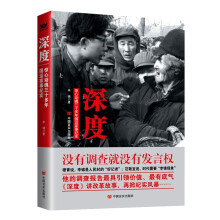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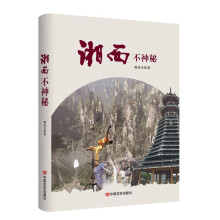
« 一部中国自由攀登者的史诗,一群不同时代的年轻攀登者在山上跨越生存和死亡的故事——中国自由攀登者的历史延续了整整二十年,却始终没有人完整、详实地描述过他们的生命处境。这些技术高超却又不屑于攀登珠峰的年轻人是中国真正的登山者。他们只有寥寥几百人,却是中国死亡率最高的运动群体。遇难者的平均年龄仅有31岁。作者在书中把这二十年用四条线索串连、交织:自由之魂(2008—2012年),刃脊探险(2002—2017年),白河十年(2004—2014年),梦幻高山(2016—2012年)。他站在每一个年轻命运的人生十字路口上,记录中国自由攀登者的真实故事,通过他们的生命轨迹透视他们生活过的那个时代,书写了一部不为人知的登山史诗。
« 记录一个个为了朴素理想行走在悬崖边缘的人,反抗主流、快乐至上的人,在世俗意义上甘愿失败的人,捕捉他们跃动的心灵和对自由的向往——这不只是一组登山者的群像,更是一个个不同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在悬崖边追寻自由与自我的故事。他们就像是社会的切片,折射出不同时代、不同个体的价值选择与人生际遇,以及人类共同的灵魂底色。他们有着迥异鲜明的性格与截然不同的命运,却在身体力行地告诉世界,他们甘愿用死亡的风险与代价换来可以超越一切的自由意志。他们未必拥有完美的人格、出众的资质,但他们的心灵却是充盈的、自由的,而这可能正是这个时代最缺少的东西。
« 呈现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和羁绊,从可见的结组、搭档,到不可言说、隐秘传承的精神共同体——我们在书中看到登山搭档通过一根绳索联结,把自己的性命安危交给对方;看到山难发生时、2008年汶川地震时,成百上千名中国户外爱好者集结成队,组成几十支救援队参与救援;看到曾经的论坛时代人们在线上的真情互动;看到白河攀岩的村民之家成了攀岩者的聚集地;看到阳朔曾经的嬉皮士生活;看到一代代登山者共同塑造了山岳的文化与历史,而大山又贯穿着这些登山者的一生。“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是这片大陆的一部分、整体的一部分。”
« 大量采访,扎实研究,严谨的事实核查,成就四十四万字长篇非虚构力作——作为资深登山爱好者,作者有长达十四年的在场/旁观经验;作为行业内资深媒体人,作者在工作中深入登山圈层的内部与攀登文化的内核。从消失的赛博空间到空气稀薄的雪山之巅,从千万字的海量素材到各语种文献资料,作者耗时近三年,大量走动、阅读、采访、调查,在书中全景式地呈现出了亲临现场般的生动场景与真实故事背后的戏剧深度。全书注释与信源多达1118条,所有必要之处,在书末注释中均有据可循,那些人物背后更不为人知的故事,在注释中也能详细探究。贴近人物的第三人称叙事,构思精巧的文本结构,充满张力的故事情节,那些宿命般的人生在纸张间徐徐展开。
« “挥着翅膀不再回头,纵然带着永远的伤口,至少我还拥有自由。”——封面由翅膀组成群山,象征每一代的登山者既是自由之翼,也是崇高之山,召唤着后来者去挑战。高山亘古不变,象征着纯粹与永恒,但登山者却是一代又一代、一拨又一拨地走进山中,振翅高飞,体现了自由攀登者走向高山、追寻自由意志的过程。
关于“自由攀登”——“自由攀登”,是指在攀登过程中,不借助任何器械之力,单纯依靠登山者自身的能力完成一条攀登路线。在这种情况下,安全带、绳索等技术器材只能被用作保护攀登者,却不能当作借力攀爬的工具。“自由攀登”在中国又被扩展成更广泛而深刻的概念:“自由”成了描述攀登者生活状态的定语。
本书讲述了过去二十年来,中国自由攀登者用攀登书写各自的命运,在山上跨越生存和死亡的故事。自由攀登者是中国特有的一群人。他们只有寥寥几百人,却是中国死亡率最高的运动群体。遇难者的平均年龄仅有31岁。本书作者通过采访大量人物、挖掘大量碎片化资料,站在每一个年轻命运的人生十字路口上,记录中国自由攀登者的真实故事,通过他们的生命轨迹透视他们生活过的那个时代,书写了一部不为人知的登山史诗。这不只是一组登山者的群像,更是一个个不同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在死亡的悬崖边追寻自由与自我的故事。他们在身体力行地告诉世界,他们甘愿用死亡的风险与代价换来可以超越一切的自由意志。
只有在山上,严冬冬才能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在一个空旷的、不适合生命生存的环境里,你自己散发的生命力,自己是可以敏锐地察觉到的,”严冬冬说,“你觉得自己心脏在跳。我知道自己的心脏会比很多人每次泵出来的血要多。这种感觉是很实在的,一种自己的存在感。”
在山上,每一次迈出脚步,每一下挥动冰镐,心脏就会“咚咚”地狂跳。这心跳的声音就好像他的名字。他挥起冰镐,咚咚;他砸向冰壁,咚咚;他迈上脚步,咚咚。严冬冬突然从20米高的冰壁上坠落,先是砸在冰壁中段,之后顺着10米高的冰坡一路滚落在地。他的左侧额头最先承受着身体与坚冰碰撞所产生的冲击。头盔里的缓冲泡沫震出裂纹,眼镜碎裂,眼睑刺破。严冬冬坠地后,脸颊紧贴着一地碎冰,左额迸流出的一小摊鲜血,把透明的冰块染成比冲锋衣还深的红色。周鹏迅速降下冰壁,趴在地上查看搭档的伤势。严冬冬趴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几分钟后才开始断断续续地说出话。
2012年元旦,在石家庄的这次攀冰冲坠事故,几乎要了严冬冬的命。他的左侧颅骨被撞成凹陷状,就像个瘪气的足球。剧烈的撞击造成轻度脑损伤。他完全不记得医生缝合伤口之前发生的事情。他很倒霉——冰爪脱落、保护点失效;也很幸运——没有从20米的高空直接拍到地面上。他还活着。在玉龙雪山冲坠之后,死亡来得更近了。
这一次死亡贴面而来。严冬冬依旧不恐惧死亡。他还会刻意训练自己,在陡峭的地形上练习危险的倒攀。“我还是会继续攀登,还是会继续很投入地做这种‘具有内在危险性、真正可能导致严重受伤或死亡’的事情,这没什么,”在事故两周后,严冬冬在博客里写道,“因为喜欢所以选择去做,因为足够喜欢所以愿意承担一直做下去可能会造成的后果。”
不恐惧死亡不等于想去死。他或许真的能做到无畏地直面死亡,但冲坠事故的阴影本能地根植在他内心深处,久久未能消散。在之后的一个月里,严冬冬在冰壁上畏首畏尾。他的搭档观察到,严冬冬的肩膀根本不敢离开冰壁,他并不是身体上做不到,而是心理上就恐惧。
严冬冬第三次深刻地思考死亡的另一重本质:责任。短短三年之内,严冬冬就经历了爱德嘉峰山难、李红学婆缪峰失踪、陈家慧遇难、哈巴雪山山难的冲击,以及数次命悬一刻的瞬间。他在山里亲眼见过数具遇难者的尸体,也目睹了一场山难、一个年轻生命的消失,会给他的搭档和家人造成多大的影响。
绝大多数自由攀登者,从不忌讳谈及死亡。他们都清楚地知晓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然而,死亡并不是一件只关乎自己的事情。事故发生后,死亡的阴影还继续笼罩着那些幸存者。对于登山者来说,死亡来临的时候,搭档可能是在最后一刻留在自己身边的人。这时死亡就变成了一件很现实的事情。
严冬冬、周鹏和李爽时常讨论万一在山上死掉的后果:搭档的遗体怎么处理,家里的老人怎么赡养,房子如何分配,遗产如何交代。“客观来讲,我们都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总要去面对,”周鹏说,“但谁都不会想到这是自己,谁都不会想到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人。”
4月28日,严冬冬在博客发布了著名的《免责宣言》,并解读撰写这篇宣言的初衷:“很简单,只是希望如果有一天我在登山时挂掉,不会有人因此而给我的搭档施加压力。作为成年人,如果我自愿决定参与某一次登山活动,那么应当为这一决定负责的只有我自己。”
这篇免责宣言并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但对于十年后的自由攀登者们来说,远胜任何律例——
我,严冬冬,现在清醒地宣布:
我理解登山是一项本质上具有危险性的活动,可能导致严重受伤或死亡。我认为,选择参与(包括发起)登山活动,意味着选择接受危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在做出所有跟登山有关的决定时,我都会把这种危险性考虑在内,这样的决定包括选择什么人作为同伴一起登山,以什么形式攀登什么样的山峰和路线,等等。
我清楚,在我与我选择的同伴一起登山时,我的生命安全许多时候取决于同伴能否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做出恰当的反应和举动。我也清楚,登山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情,登山者(包括我自己和我选择的同伴)在面临这种挑战的时候无法保证总能做出恰当的反应和举动。
我认为,如果在我自愿选择参与的登山活动过程中,我因为任何并非我自己或同伴故意制造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我自己不恰当的反应和举动,同伴不恰当的反应和举动,意料之外和意料之中的山区环境客观风险等)而发生严重受伤或死亡的情况,那么我的同伴不应当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解释和赔偿的责任)。
2012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