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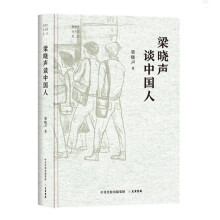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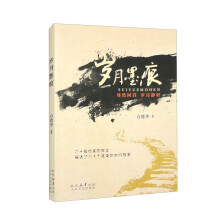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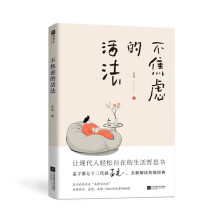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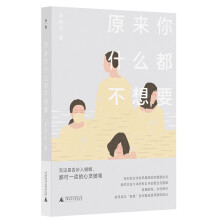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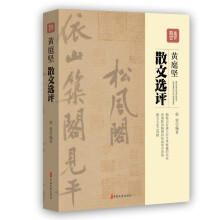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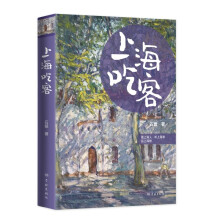

我早已不再是那个在博物馆凑近名画合影留念的青年,回国数年,也和那位《纽约琐记》的作者日渐疏远:写作使我从只顾画画的痴态中醒来,醒在自己不同的书中,暗暗惊讶域外和家国怎样深刻地改变并重塑一个人。
美术馆
美术馆应该算是领会形式、评判形式的最后场所吗?
——杜尚
孩子喜欢打量穿制服的人。我也喜欢。在这儿,警察的黑制服和一身披挂当然最醒目:帽徽、肩章、警衔、枪、子弹带、手铐、警棍、步话机,外加一本记事皮夹。有一回我在地铁站点烟,才吸半口,两位警察笑嘻嘻走拢来,老朋友似的打过招呼,接着飞快填妥罚款单,撕下来,递给我。
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到处都是警卫,一色青灰制服,但行头简单,只是徒手,每座小馆至少派定一位。当你拐进暗幽幽的中世纪告解室、古印度庙廊偏房或埃及经卷馆,正好没有观众时,必定先瞧见一位警卫呆在那里。文艺复兴馆、印象派馆,设在顶层的苏州亭院,男女警卫可就多了,聊天,使眼色,来回闲步。在千万件珍藏瑰宝中,他们是仅有的活人,会打哈欠,只因身穿制服,相貌不易辨识。人总有片刻的同情心吧(也许是好奇心),当我瞥见哪位百无聊赖的警卫仰面端详名画,就会闪过一念:三百六十五天,您还没看够么?
警卫长不穿制服,西装笔挺,巡逡各馆,手里永远提着步话机——闭馆了。忽然,青灰色的警卫们不知何时已在各馆出口排列成阵,缓缓移动,就像街战时警民对峙那样,将观众一步步逼出展厅。这时,将要下班的警卫个个容光焕发。
大门口还有一道警卫线。当我在馆内临画完毕,手提摹本通过时,警卫必须仔细查证内框边缘和画布反面事先加盖的馆方专章(但从不瞧一眼我的画艺),确认无诈,这才拍拍我的肩背,放我出馆,就像小说《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探完监,挤过门口时被狱卒在背上拍那么一记。
只有那位肥胖的老警卫每次都留住我,偏头审视摹本:“哈!艾尔?格列柯,不可思议。你保管发财——等一等,这绝对就是那张原作,你可骗不了我!”
老头子名叫乔万尼,意大利移民。如果不当值,这位来自文艺复兴国的老警卫可以教我全本欧洲美术史呢。
1982年元月,我踏雪造访大都会美术馆,平生第一次在看也看不过来的原作之间梦游似的乱走,直走得腰腿滞重、口干舌燥。我哪里晓得逛美术馆这等辛苦,又不肯停下歇息。眼睛只是睁着,也不知看在眼里没有。脑子……
修订版序
封面总要重新弄过的,适可将前两册书样子缩小了,印在封底上,算是此书前身的如实交代;图片则大可添换——书中写到邱岳峰,结果邱公子辗转寻到我,赠我邱先生早岁与晚年的照片;有一篇说及早夭的钢琴才女顾圣婴,也给我获得她生前的丽影;又有学者徐宗懋送我从未面世的蔡元培林语堂等民国前辈老照片,都是难得觅见的影像史料,补入书中,正合适:末尾有几篇涉及民国的教授与教师,当时下笔,哪想到自己翌年会有受聘教书的机缘,近时重读,颇惊讶怎在七八年前即已留心国内的教育和大学……文字内容,则补进两篇遗漏稿,太过短促而油滑者,删除二三,其余照旧:倘若读者不嫌弃,当然很感激,但我是作者,赠书到手,好意思送人么?我知道,若是诚心巴结旧雨新知,莫如多写新篇幅,无奈我不再如那些年有闲空。即便零零星星写起来,新书起个什么题目呢?眼下,只能预先谢谢再次破费的读者,并请对这本书的修订与再版,多多包涵。|
——《多余的素材》修订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