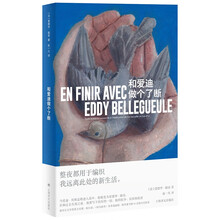初秋的空气是那么美妙空灵,那么奇异透明,附近所有的景物都显得更近,更清晰——河对岸的每一片叶子,每一根树枝似乎都能用双手抓住。
——雅科布·A. 里斯①
①Jacob August Riis (1849—1914),原籍丹麦的美国记者和社会改革者,最早的纪实摄影师之一。
第一章
“人类的法则告诉我们,人生就像一座迷宫,到处是死路和上锁的门。有时候你不得不转身朝后走一段路,重新选择方向,但不要放弃希望。”
广播信号“嘶”的一声消失了,就像一根头发烧成了灰。
“该死的。”司机嘟囔着,用手指敲击着那镶在红木框架里闪着蓝光的收音机。
“打起精神来,我们要听卡尔·伯恩斯坦的爱人①[1]播音,她可真他妈的有意思。”部长说,笑得肩膀乱颤。
“丹麦广播电台。现在发生了一点技术故障,我们正在努力排除。”
“这不是我的错。”司机小声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丹麦广播电台。现在发生了一点技术故障,我们正在??”
“关掉关掉!”部长大声嚷嚷着。
我挤出一个微笑。我实在不想跟那傻瓜再说一遍,卡桑德拉是我多年的朋友,不是爱人。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她是同性恋,至少也是双性恋。我攥紧了手中的公文包,空气中可以嗅到新鞣制的皮革气味,那是卡桑德拉送给我的礼物,她从尼泊尔带回来的手工缝制皮包。部长自得其乐的时候一定要当心,他的好情绪随时会消失,在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已经落入圈套,不得不在他为下属即兴设置的冲突中自卫。他的下一段台词很可能是:“我凭什么要听你爱人的广播?”或者:“你笑话我,是不是?”他认为有责任让我这样的官场暴发户明白,不要以为屁股已经坐稳。他一定会把我看得更紧,并向我显示:外交生涯有其代价,这代价极其高昂,只有那些最有才华、最努力,而且最冷酷无情的人才能最终穿过针眼①[2],得到人人垂涎的大使职位。其实我具备所有这些必要的素质,只不过身旁这个精神病不知道罢了。
“现在彻底完了。”司机一边说,一边按着按钮。他停在另一个频道,震耳欲聋的流行乐突然从四面八方响起,我们活像交叉火力网下的士兵。他还没来得及关掉,部长就嚷嚷起来。
“你也完了!还不赶紧关掉它。”
“对不起。二十五秒后到达。”司机低头对着手腕旁的对讲机说。
他当过特种兵——我看着他那公牛一样堆叠了五层肌肉的脖子想道。
“这次你一定得完全记住,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伯恩斯坦书记官。当我们今天离开外交政策委员会的时候,这件事就彻底了断了,明白吗?”他斩钉截铁地说,眼睛不看我。
我认识他多年,但我们从来没有对视过。他无疑要将这种过于个人化的目光接触留给家人——目前包括一个两岁的女儿和第三任太太。流言说他仍然和前任太太们纠缠不清,不再见已经长大的前房孩子们。他追求那些显然比他年轻、模特儿式的美丽女人。他对卡桑德拉也有某种兴趣。她四十岁了,看上去只有三十。人们想不到她会有一对十八岁的双胞胎儿子在家里晃荡。部长曾在一本女性杂志上看到过她的照片,她裸身站在林边的白桦树之间,长发像轻柔的丝绸一样在胸前飘荡。
我研究过这位部长。他的无边眼镜后面有一双多水的眼睛,眼白上堆积着黄色的脂肪,上面布满红色血丝。眼袋突出,面颊上爆裂的毛细血管纵横交错。他的牙齿是石灰白的种植牙,就像华盛顿和好莱坞那些名人一样。现在他已经跳下了车,走完一半台阶,后面紧跟着两个保安人员,我拿着公文包和一大沓文件,还没来得及挪身到车外。他打开克里斯钦堡①[3]的大门,脚步像敲鼓一样重重地落在地板上,我赶紧跟在他后面。
“那个傻瓜转台之前她在说什么?”他瞟了一眼正对着手机讲话的司机,“是不是理想主义的骗局,合作共同体,新法律什么的?”
“我没听见,他关机了。”我喃喃地说,侧身进门,跟在部长后面走过楼梯口的岗亭。
“人类的法则。”她是那么说的。“那是什么鬼玩意儿?”他笑了,“我一定努力让它在议会通过,我们大家就会成为真正的人类,然后退休,让丹麦驶向共同体的汪洋大海。”
部长的笑声变成了嘶哑的老烟枪咳嗽。他皱着眉头吞下一口痰。我们走在陡峭的楼梯上的几秒钟里,他脸上浮现出怪相。之后,他沉默了,屏住呼吸。
部长有一种出类拔萃的自制力,对此他也非常得意,他甚至把这种能力传给了孩子们。这是他送给后代最好的礼物,他在《星期日报》的一篇人物专访中这样说。他每星期至少要上一次媒体。记者们喜欢他粗鲁的魅力,他也准备好随时发言,并高效地听取智囊的建议,而在正式场合则对智囊嗤之以鼻。
我足够了解他,知道此时此刻,因为缺少尼古丁补充已长达几分钟,他正在真正的好奇心和后果难以预知的非理性爆发之间走钢丝。我沉默不语。我绝不能分散注意力,不能犯更多的错误。那天我在外交政策委员会给了部长错误的信息,导致反对党在媒体上骂他是说谎者,从而铸成大错。这事黏在我身上,就像是传染病。部里的同事们都躲着我。换成别人我也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错误,是零容忍文化里最大的忌讳。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处在更严密的监督之下。体制高层的关键人物对我大为失望,人人都知道,我事业的前程明显地黯淡了许多——如果在别人眼里曾经辉煌过的话。毫无疑问,我面前永远站着一个准备好随时接替我位置的同事。只要再犯一个错误,我就会在专门为体制淘汰出来的苦命人准备的位子上了此残生,比如特别顾问什么的。除非能设法离开外交部,到别的地方去试运气。但我早已不再考虑离开。我已经四十二岁,正在一步步接近那据说是高不可攀的目标。只要咬紧牙关在哥本哈根再坚持一年,就可以外放到广阔的世界,三四年后回国来担任一个副职。如果一切顺利,再过半年就会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和女王指派的官员,通往神圣大使职位的道路就此敞开。阿门。我经常说,要在满五十岁之前实现这个目标。这样,三十年无意识的埋头苦干将换来二十年梦想中的高薪职位,非人的工作努力将收获丰盛的成果。这想法让我飘飘然,但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就不敢再想下去。
出事了。周围人们的动作活像受遥控的机器人。他们从各自的办公室出来,手机贴在耳朵上,在走廊里机械地走来走去,像焦躁的母鸡一样撞上墙壁,也互相碰撞,对着那小电子设备嘀嘀咕咕。
“活见鬼!”部长嚷嚷着,国情局①[4]来的保镖不由分说架起他的胳膊就跑。“紧急情况,马上离开大楼!”其中一个保镖对我大声说。
我站在走廊中间,目送他们顺着通往紧急出口的楼梯走下去,消失。周围的人在四处奔跑。部长的智囊,那屁股被短裙绷得紧紧的女人正在拍击手机。
“丹麦酒店被炸飞了!”她嚷嚷着快步走过,突然站住,转过身来,“天哪,你的爱人。”她的嘴一张一合,朝我走过来一步,“我希望没??我得去找部长。”她消失在人群中。
我看着外交部长的讲演稿,那是我上午早些时候写完的。这些纸片就像笨重的天鹅腾空而起,飞向天花板,撞上墙壁,再坠落到地板上。我颓然落坐于墙边一把浅蓝色的洛可可式椅子,看着外交政策委员会门上方的挂钟。时间是十二点五十四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