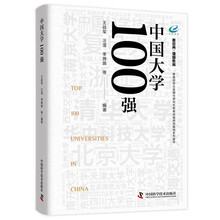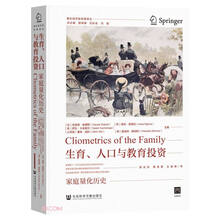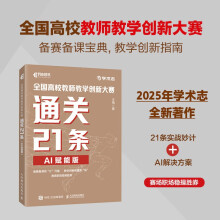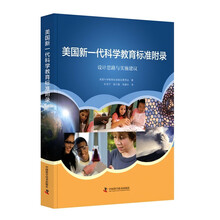《教学文本及其阐释》:
一、墨守成规,不见形式形式是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本形式的理解、把握能力是学生语文素养的重要体现,也是语文考查的重要内容。笔者之所以会涉足文本研究,最初动力便是教学之需。面对内容性试题,学生不管肚里有货没货,总能“咿呀”两句,写上两行文字交差。可面对形式类鉴赏试题,许多学生真是一筹莫展,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面对这样的情景,作为教师心里怎能不着急?可是,在教学中就是有部分老师完全不顾文本中的形式,只是干瘪地重复教参的内容。比如沈从文的《端午日》,我在网上查看了许多教学设计,几乎都是一个模式,端午节有哪些习俗,边城地方人是如何过端午的?课文描绘了一幅怎样的画面?就是忙着引导学生回答这些内容问题。说实话,这些问题哪里需要教师来引导,学生自己看看书也都能答出来。换句话说,这样的教学,其实是在浪费学生的时间,更是在败坏学生学习语文的胃口。笔者在教学《端午日》时给学生提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就《边城》中一句话说的。在《端午日》节选文字之前,沈从文说:“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与过年。”①我的问题就是,沈从文说了三个节日,可真正写的只有端午,为什么?二是就端午的习俗说的。一般说来,端午芾大家都会吃粽子、赛龙舟、扣五色丝,可《端午日》只写赛龙舟,吃粽子、扣五色丝等至今仍然深入人心的习俗何以在小说中只字不提呢?第三个问题是就文本的最后一节说的。文本(节选)最后一节,写了一个军民追赶鸭子的场景,这是一个其他地方都没有的习俗,作者为什么要写?这几个问题都涉及到情节的选择问题,而情节选择又涉及到人物性格的塑造问题。沈从文要塑造一个健勇的傩送形象,吃粽子显然不行,扣五色丝更不行,于是只有赛龙舟了,而且赛龙舟又具有地方特色,于是就成为沈从文的首选了。
这里得要加两句说明,来说一下对于“形式”的理解。在不少人的观念中,只有像“朦胧”“张力”之类西方学者创造出来的概念才算是真正的形式。我以为这大可不必,所有与文本创作相关的表现手段都是形式,而且那些与文本内容息息相关的主题、题材类内容如主题的提炼、题材的选择等具有形式意味的因素也应当归入形式的范畴。这样一来,课堂上可讨论的问题便非常丰富,而且,这一学习内容对其写作水平的提高益处更大。
为什么有些老师的课堂上总是缺少形式的因子?我理解,这与其长期接受“作品”的观念有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品观一统天下,读作品就是了解其内容,要了解作品内容就是要了解作者的生平、创作的时代背景等。长期以来,社会学的解读方法几乎是唯一的文本阐释方法。长期与外界隔绝,自然无法理解“有意味的形式”这样带有浓厚西方色彩的语言,于是也就慢慢地与形式分道扬镳了。
二、画地为牢,不知圆融
就总体而言,文本教学的情况不怎么理想,尤其是在现代文学意义上进行的文本教学就更是如此,这其中既有老师的因素,也有学生的因素。在老师方面,普遍对西方现代派文学了解不多,知识储备不足,因而也就很难胜任教学。在学生方面,则是受碎片化、快餐化阅读影响,一味追求快感,不愿动脑,不想思考,常以“读不懂”“读不惯”推脱了事。
可也有些老师,因为个人爱好而大量阅读了西方现代派文学,对蕴藏在文本背后的西方现代语文形式相对熟稔,因而常表现出文化优越感,以西方文学正宗传人自居,视常见的诸如即小见大、卒章显志之类语文形式为落后,从而划西方现代派文学之地为牢,表现出另一种形式的墨守。比如教学卡夫卡的《变形记》,即要求学生借此理解表现主义致力表现以取代再现的文学主张,探究表现主义的艺术特色,甚至探讨表现主义的历史地位,并在言谈举止间不自觉地流露出中国文学落后的意念。应当说这样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教材的设计初衷。沪版教材为此配置了三道思考练习,两道与内容相关,一是“体会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的心理,仔细琢磨这些心理活动所反映出的长期充当小职员的格里高尔的处境和心境”,二是试根据节选内容推断“格里高尔最终有没有‘进入人类的圈子”’。一道是探究语文形式的,即“把虚幻和现实结合起来是这篇小说主要的艺术特色,试从课文中找出若干细节来加以阐述”。①在这一语文形式题干中,没有看到学者们探讨《变形记》手法时常说的“荒诞”、“陌生化”等字眼,而代之以“虚幻”一词,相信“虚幻与现实的结合”这一说法是经过教材编辑仔细推敲的。这一说法也比较明确地传达出了编者对现代派文学的总体态度,即既要睁开眼睛观察世界,又要表现出自己的文化定力,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去评判世界,而不是盲目崇拜,自乱阵脚。而且三道习题的配量比例也显示了编者的态度,即对于像《变形记》这样带有浓郁现代派色彩的文学作品,教材的关注重点也还是内容,还是人,还是人的生存状况。在这里,技巧是从属于主题的。教材的这一编码破译很重要,因为它等于在交给我们一个价值评判坐标。有了这一坐标,以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作品,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我们都会心中有数,也自然能应付裕如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