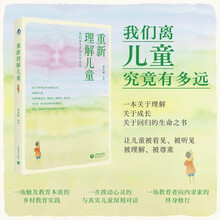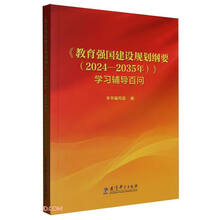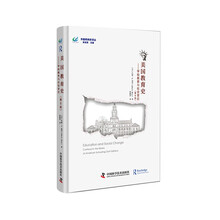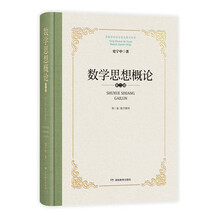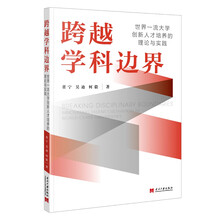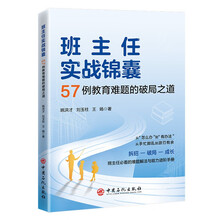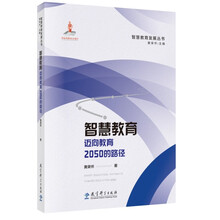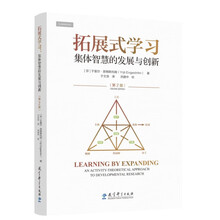《高校名师与教师职业发展丛书:名师谈教学(感悟篇)》:
我并不是说教学中不体现学术的创新,不引导学生向创新学术的方面发展,我只是说本科生正在打基础的阶段,学术创新应该同强调扎实读书、培养求实的学风结合起来。
事实上,只从阅读、铨解的方面说,古代、近代一些人的注释评说中,确实有许多不正确、有待后人订正、补充的地方。比如《楚辞·离骚》“余虽修娉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王逸解释说:“言虽有绝远之智,娉好之姿,然已为馋人所鞿羁而系累矣,故朝谏謇謇于君,夕暮而身废替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影响较大的几种注本大体都按王逸之注作解,有的大学教材也同王逸注。王念孙《读书杂志》中列出几条证据,说明先秦典籍中“唯”字借作“虽”。这是完全正确的。但王念孙解释上句说:“言余唯有此修娉之行以致为人所系累也”,仍未摆脱王逸注误说的影响。因为这个“唯”字关下“修娉”与“鞿羁”两层意思,“以”的作用同于“而”,为连词。这里屈原的意思是:我只是因为有此修姱之行,又不放纵胡为,故早上犯言直谏,晚上即遭贬斥。王逸为东汉人,去屈原时代毕竟只有四五百年,其注吸取了汉代各家关于《楚辞》的注解,他所据各书都已散佚不存。王逸又是楚故都宜城人,他的注是释读《楚辞》最重要的依据;王念孙是清代著名的朴学大师,他的《读书杂志》等书中精见叠出,论一事往往证据丛集,几不可移易,但也难免有值得商榷之处。则其他书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我说,我们在教学中还是要注意引导学生的探索、创新精神,只是要同严谨、求实的作风结合起来。代数、几何、物理等自然学科有定义、定理、公理,人文学科没有这些,不等于人文学科可以完全凭借主观想象胡说,它也有些必须要遵循的原则。要把中国古代文学学好,除了能认真读作品这一点之外,还要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基础:
(1)文学理论、文艺美学、心理学的基础;
(2)文字、音韵、训诂与文献学基础;
(3)古代史与古代文化方面的基础,包括历史、民俗、官制、历史地理等在内。
没有这三个方面的基础,不但难以解决问题,也难以发现问题。这三方面的知识如鼎的三条腿,支撑着一个鼎身——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我们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是要培养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给他们指出怎样才能做到容易发现问题和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医学的教学,如何才能准确诊断出病人的病情,如何才能做到对任何一种病都能很快提出治疗方案,并且实施之后有好的疗效,而不是单方面鼓励学生大胆设想、敢于提出任何结论。我认为本科生教学中首先应强调扎实读书,读作品,读相关研究性著作和相关基本理论著作,以使自己手里多几把打开学术奥秘之门的钥匙,多几种解决问题的工具。
我自己的一些研究,也是在长期读书、积累的基础上完成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屈原《橘颂》的作品时,大部分学者认为其情调轻快,其形式也与《九章》中其他篇不同,应是青年时代的作品,也有认为是中年或老年时期作品,甚至有主张是屈原的绝笔者。屈原已死两千多年,无法起诗人于江海之中而问之,便给一些学者的“学术创新”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似乎这个问题再无法解决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读《仪礼》时发现《士冠礼》篇所载八首冠词,在形式上同《橘颂》一样,都是四言,内容也都谈到“德”(“以成厥德”、“秉德无私”),内容也都侧重要美其德行、增其内秀等,有的词语同《橘颂》大体一样,如“弃尔幼志,顺尔成德”等。看来,《橘颂》是屈原在二十岁行冠礼时所作,表现了他青年时代的志向。古代冠词也称为“颂”,《孔子家语》中有一篇即名《冠颂》,而且其中有一句“去王幼志”也同《橘颂》中的“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相近,都是说从此要去掉未成人时的一些想法,树立大志。那么屈原的为什么借橘树来抒发情感呢?因为楚地云梦之橘在战国之时很有名,《战国策·赵策二》记苏秦合纵说赵王说:“大王诚能听臣,燕必致毡、裘、狗、马之地,齐必致海隅鱼盐之地,楚必致橘柚云梦之地……”,则云梦之橘是楚国丰饶土地的象征,故屈原用以自喻。所以,我以为定《橘颂》为屈原二十岁时之作,不但究竟作于屈原生平哪一阶段的问题得以解决,作于哪一年也可以确定。但如果不是读了《仪礼》、《孔子家语》,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所以,我一直主张本科生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多读书,在读书中思考问题。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