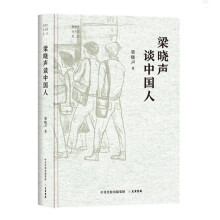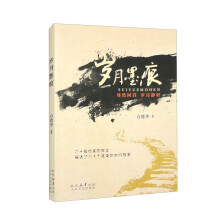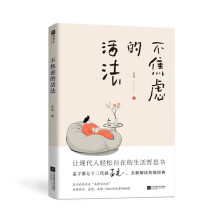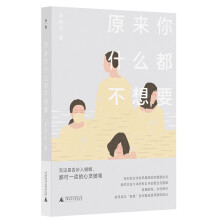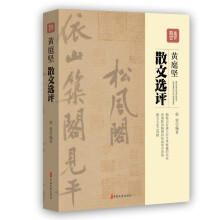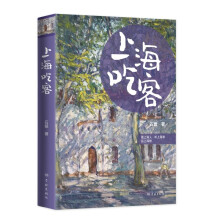地、草木、麻雀、胡蜂、田野、节气,有居住地以外的陌生的小城或乡村,有精神上契合的友人,有书籍,和因书籍衍生出来的人和思想,但没有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在四姑身上,一个敦厚女子对土地与书籍的同时热爱,造成了她最终命运的无限悲剧,如果没有书籍,也许她不过是农村寻常女儿家,嫁寻常汉生平常子都是理所应当的事。可是,她偏偏热爱读书,她身上的如大地一般的温暖的人性,在对婚姻的顺从和接纳中变得冰凉而无奈。苇岸用完整的篇幅写了他的四姑,是因为,他不仅仅将她看成是他的亲人吧。四姑更像大地,更像大地上的一株草木,也更像从土地上升腾而起的精神的图腾。她生得不美,但她又有着来自土地深处的无可比拟的美,而这种美又因为悲剧性的命运得到了再一次升腾,这种气息,是很多写作者深深迷恋的悲剧之美。
我甚至残忍地想到,如果苇岸还活着,如果他的母亲死了,他的兄弟死了,或者,他的四姑死了,他会写下怎样的文字?他看待世界的眼光会变化吗?他的情绪、心境会改变吗?在他的书里,在他的大地上,他从来都充满欣悦和敬畏,只要是由大地而来的,就没有丑恶的和不能被接受的。“这是一具雄蜂的尸体,它是自然死亡,还是因疾病或敌害而死,不得而知。它偃卧在那里,翅凌乱地散开,肢蜷曲在一起。它的尸身僵硬,很轻,最小的风能将它推动”。苇岸描写他所见的事物,从未将自己的情绪强加于人,他不说他哀愁,不说他震动,不说他欢欣,他似乎从来不使用感叹号。他只是描述出来,你自去领悟。而这种不动声色,力量更甚。
在我的生命空间里,亲人占据了很庞大的部分,他们是我难以逾越的山岭,横亘在面前,几乎所有的情绪都被牵制。12岁那年,我10岁的小妹病死了,她身上穿着结了血痂的硬邦邦的小棉袄,卷在一面小席子里。29岁那年,妈妈病死了,她以跪伏拜祭的姿势抵抗疼痛,但苍天没有怜悯她。2010年7月,我的哥哥病死了,他在最后的日子里使用杜冷丁镇痛,最终精神错乱,没有留下一句清醒的话。
在苇岸1990年11月20日的日记的最后,记录了伊本·哈兹木的句子:“离别之际,四分之三的痛苦归留下的人,离去的人只带走了四分之一。”
但是,对我的哥哥来说,因为最后的精神错乱,他成了一个空心人,他空手而去,留下了四分之四的痛苦。
在他病中尚清醒安好的时候,虽时有疼痛,但交流很多。那时的他,语言和精神,都很接近苇岸。他提起一片被人丢掉的仙人掌:“它被丢在垃圾堆里,被太阳晒得完全干掉了,但有一天下了雨,再看见它的时候,它已经站起来扎根在土里,干扁的身体也复原了。后来,有同事不信这生命的魔力,将它拔出来抛到房顶上,下了几场雨后,我们看到,那片仙人掌绿生生地站在瓦片上。”哥哥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都满怀信心和欢乐,我们把这些话当成一种象征,他一定有着敢于和病魔抵挡无限个回合的勇气,直到战胜。
哥哥是养花的好手。别人的菊花,只有秋天才顺时而开,而哥哥的菊花,四季都能开。别人都惊异,以为有什么秘诀,他只是淡淡而笑,说花儿都是有情感的,要怀着柔情爱意去侍弄它,要观察它的喜好变化,顺着它的脾性养护,最终,花儿对你也就有感情了,它愿意为你不断绽放。若苇岸听到哥哥这些话,他可能会视他为知己的。在哥哥的天性中,有诗意与纯美的一面,若他接近和热爱文字,也许会是苇岸喜欢的诗人,或者,即使他离文字和精神很远,也一定是苇岸喜欢的普通人,因为,他身上有草木的品性。
然而,又能怎样呢?正如大地、河流、风、天空无法挽救热爱着它们的苇岸一样,仙人掌、菊花和心向自然的气场同样不能借力给我的兄长。他们都死了,苇岸死于1999年5月,39岁,我的兄长死于2010年7月,37岁。
苇岸在临终的前几天留下了他最后几句话,他口述,他妹妹执笔记录,他的思维缜密、清晰,出人意料地镇定和冷静。可是,我知道,这些话必定是断断续续、耗费了极多气力的,而且,他必定在强忍和抵御一波波袭来的要命的疼痛。苇岸毕竟是苇岸,他留给我们的这些话里看不到他瘦成一副骨架的可怕样子,看不到他被疼痛煎熬的苦苦挣扎的样子,他把自己当成祭品了,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鲜血浸透了袍子,他还在赞美,忏悔,祈祷,救赎。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