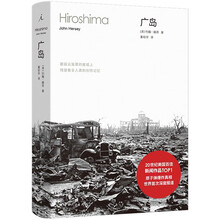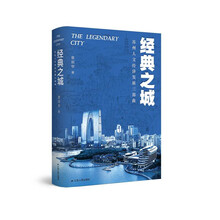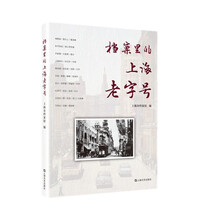《囚居丛书:遭难前后》:
1 人民立场的我 我是一个极寻常,毫不足道,碌碌无能的一个中国女公民,这是我自己知道。不但如此,连朋友也以此默许我的。当中国军队退出上海,许许多多中国士兵被驱赶到租界里来的时候,就在霞飞路杜美路旁的一角,后来是叫作蓝维纳公园的所在,那时是被称为“民生简便食堂”的烟囱高高的经常张开口喷着浓雾,想以人间的一角生活,写在素洁如雪的天幕上,报道这里也有在为贫苦无力享受豪华的餐席的,为这批可怜的人们服务者,但就因为只有为可怜的人们服务的地方,才肯收容那被政府力量所不及保护的兵士,虽然包围着这兵士四周的还有千千万万的自国人民,连我也在其内。
铁丝网障隔着兵士与人民的会晤,大家走过,都不期抱着焦燥,难堪与无可奈何的心境。铁丝网的严重性一天天在增加,包围了手无寸铁的兵士之外,又在包围着手无寸铁的人民,大家一致承认:是在大的集中营里生活着。有些人在计划脱逃,走入更自由的天地去,有些人却不能脱逃,也计划用甚么方法就近掩藏一下,“狡兔三窟”,当心点总比较是好的。在这种不安定的情绪之下,朋友相见,交换意见之后,总是说:“你可以不走因为你向来就没有做甚么事,而且日本人对鲁迅先生也很尊重,绝不会对你怎样的。”这朋友的说法一点不错,我自己细加检讨,的确也没有担任过什么,整天在家里忙着,无非是日常生活的布置,并没有什么值得提上口头的,值得令人满意,可以因而骄傲的工作过。我有什么可怕的呢?为了体质当时并不算强壮的孩子,我不敢带着他奔波遥远的路程,有时甚致要步行或沦落的旅途,除了准备把生命交出,像弃掉废纸一样的毫不吝啬,否则能维持一天苟安的生活,我总想等孩子身体稍好,经得起流浪再行出门。然而第二个问题又来了,我这一个家,这毫没有贵重物品的家,在有些人眼里是看不起的,但也更有些人,用精神在感召我,如同我自己一样,希望把这个家,不,这一草一木,一桌一椅,一书一物,凡是鲁迅先生留下来的,都好好地保存起来,这不是私产,这是所有全国人民,凡是要了解这一时代文化,这一位作家的生活的人,只要不是有意歪曲,像发了怔忡病的迫害狂者,见了影子也以为是鬼魅的东西,我们都愿意除此之外体会到应该有保存藏书的义务。虽则这藏书是如此贫乏,不足称道,但就是这贫瘠的土地,也曾经开出美丽的花朵和生出供给生命的米粮,这如何能自私?所以我在这种精神感召的情况之下,毅然不敢自馁,负起看守的责任。当然请别人看守也许有可能的,但是倘使连我也不能看守的时候而要求别人,为了看守这些逝去的遗留,而把活着的生命葬送,是没有理由的,因此我不敢在任何危难的时候交托任何人。以人民立场的我,始终没有离开上海一步也就为此。八周年了,一天天捱着,活着,死一样的活着,复苏一样的活着,艰苦的活着。可以说是生活过来了吗?我不知道。因此我还是想就我所知道的一部分写出来,为我的生活,以前的,和以后的作一个段落。有一位女友,在经过一年多狱中生活之后,每见人就不自觉流露出“我们在那里是如何如何的”一些话,引到听的人觉得太麻烦了。其实在讲的人并不自觉的,因为生活的对比太强烈了,好比在盛夏红日之后走到阴处,长久也会觉得烈日的可怕一样,自然不知不觉会有深刻的印象。我之所以把经过略写一二,也不过是把从太阳下毒晒过了的伤痛,稍稍写出就是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