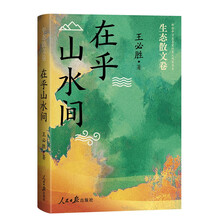认真是一种品质
时常想起这么几件事情。一旦想起来,心里便感到温暖,同时也会因自己相比之下的欠缺而觉得背脊上有点发冷。这几件事体现的是交往过程中一种很认真很负责的精神。对我而言,当事人都是长者,尊者,大家。
没赶上偷读手抄本的时髦,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念大学时在当代文学史教材里才晓得《第二次握手》的影响,作为中文系的学生对张扬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作家自然是满怀敬意。没想到过了二十多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能跟张扬一起吃饭聊天。那时他还没定居浏阳,我也早已不再是青年,彼此都因初次见面而显得话语不多。后来话说得多了是因为说到了读书,似乎两个人阅读的路径有些趋同的地方。其间我提到在某处翻过潘旭澜的《太平杂说》,我说那是一本很有思想的好书,可惜现在是遍寻书店而不可得了。张扬深以为然,当时他对潘的史论有过甚为精当的评价。记得张扬还自言自语地说他买过这书。我没太在意他说他买过这书,所以我的感觉他这是自言自语,至多也只是针对我的遗憾而流露出的一种得意。其实不然。事后有一天,收到一个特挂邮件,拆开一看,原来是张扬托他夫人陈丽女士邮寄给我的《太平杂说》!那书的封底盖的是湖南图书城的购书戳记,书却是从沈阳寄出,按理这也是张扬的心爱之物了。或者就张扬的藏书而言《太平杂说》属重本,将书赠我乃是有意让多余的一册潘著物得其所?不管是哪种情形,反正对于著名作家张扬而言,我仅仅是一位陌生的读者,他哪里犯得着为我在饭局中偶尔提及的一本别人的著作这么费心呢。在《第二次握手》重写本首发式上,我说张扬是一位很令人尊敬的作家,我就说了这件事,我说张扬这人很认真很负责。
香港叶玉超、唐璧珍夫妇不只在古体诗词领域有着极深造诣,叶的书法、唐的山水画都是了不得的功底。原来我只晓得叶先生曾为国际摄影大师陈复礼的作品题过百十余首七言律诗。这些诗在《成报》副刊连载数月,赢得好评如潮,不少读者剪贴下来宝而藏之。前些年叶、唐来浏阳参加一个古诗词学术研讨活动,听别人介绍方知他们夫题妇画,合璧生辉,早已是诗词书画界的佳话。那天晚上见到这对大概因旅途劳顿而显得甚为苍老疲惫的长者,我说了一些“久仰久仰”之类的客气话:当然是出自内心的客气话,我还说先生的题画诗里我特别喜欢那首《翠谷红梅》。第二天早餐后叶先生约我到他下榻的宾馆一叙。走进房间,让我感动莫名:桌上、地下摆了好一些楷体书写的条幅,全是《翠谷红梅》!“写得不好,你选一幅做个留念吧,我太太还要送你一幅山水画呢。”听叶先生这样说,我才知道唐璧珍女士把床铺当画板画出来的一幅山水是给我的,其时她正以半跪的姿势在床头那幅墨迹未干的画上题签。没想到我几句真诚的恭维竟把两位老人折腾如斯!从老人手中接过两幅字画时,我已无心体味其艺术魅力,心里充盈着的满是对两位老人的崇敬。叶先生说“我太太昨晚几乎一宿未眠呢。”我心下想,既如此那先生您未必休息好了?都年过古稀了,唐女士腿脚还不甚灵便呢,白天要开会参观,晚上又要赶飞机转道返港:两位老人也太认真了!
我将一册自己新出的杂文集子送剧作家陈健雅正。“雅正”其实也是客气话,人家谁会真的把你那只合自己“珍藏”的烂扫把端详个仔细还“雅正”呢?只过了三天,就接到了陈的电话,说书全看完了。美言几旬之后,便道“书里引用韩愈的诗你搞错了一个字,是‘夕贬潮阳路八干’,不是潮州”。我在电话里跟他说:“不会错的,这诗我很熟,前年在潮州韩公祠见过的石刻也是‘潮州’不是‘潮阳’,您记恍惚了?”我记得当时电话那头陈健老先生话说得不很肯定。意思是可能记错了,但是不应该记错。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和陈健一起参加一个研究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保护的会议。会议休息期间,陈先生从一个大布包里取出数卷厚厚的《全唐诗》。《全唐诗》是图书馆的,盖着印。陈先生翻着韩愈那首诗给我看:“应该是潮‘阳’,潮‘州’不对。”其实“潮州”“潮阳”都对,是两个不同的版本,此前我已翻过资料了,只是忘记告诉这位热心的长者,害得他把一部《全唐诗》查来查去搬来搬去。望着陈先生郑重其事地把书放进包里时的神情,我为自己的敷衍而羞惭,更为他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