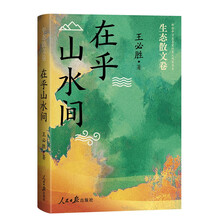《毕飞宇散文》:
我要剥削你们,逼你们干活,这个是一定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又不能忽略,无论地主还是长工,中国的农民就是中国的农民,脸面上的事终究是一个大问题,他们很难跳出这样的一种人际认知的框架,那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一方面,我要强迫你们劳动;另一方面,我又要尽可能地避免面对面。这里头就有了日常的规则,生活的规则,我们也可以把它叫作生活的逻辑,或者干脆,我们也可以叫它文化的形态。这个文化形态是标准的东方式的,中国的,那就是打人不打脸,说得高级一点,就是乡村的礼仪。中国的农民是讲究这个东西的。现在,好玩的事情终于出现了,周扒皮和公鸡产生了关系,公鸡又和长工产生了关系。这一来事情就好办多了,——不是我在逼迫你们,而是公鸡在逼迫你们。在这里,公鸡不再是公鸡了,它有了附加的意义,它变成了一个丧尽天良的地主所表现出来的顾忌。
我们不去讨论《半夜鸡叫》这个作品的好坏,我只想说周扒皮的顾忌,这个顾忌是有价值的。我不知道《半夜鸡叫》在当时是怎么流行起来的,从当时的文化背景来看,它实在是太反动了,是蒙混过关的。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还要有所顾忌么?我只能说,作者在这个地方一不小心流露出了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就叫“世态人情”。就因为这么一点可怜的世态人情,周扒皮这个老混蛋有特点了。我记得当年我们每年都要演《半夜鸡叫》,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抢着去演周扒皮。现在回过头来看,和南霸天与胡汉三这些反面人物比较起来,周扒皮更像一个坏人,进一步说,他有点像一个人了,他的“鸡叫”使他和那个时候的反派人物区别开来了,那个时候的反派人物不是人哪,是妖魔鬼怪,为什么是妖魔鬼怪呢?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谈。总之,周扒皮的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然而,说到底,又在可以想象的范畴里面。孩子们痛恨他,却喜爱这个艺术形象,他的身上存在着农民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爱占便宜,却又胆小,怕过分,当然还有狡诈。
是鸡叫构成了《半夜鸡叫》的“戏剧性”,是鸡叫折射出了周扒皮人性里的复杂面。“文革”中是没有所谓的文学的,我只能说,就在那样的文化语境里,《半夜鸡叫》多多少少沾了文学的一点边,因为它在不经意间多少反映了一些世态人情,虽然它是极不自觉的。
对小说而言,世态人情是极为重要的,即使它不是最重要的,它起码也是最基础的。是一个基本的东西,这是小说的底子,小说的呼吸。其实,这个东西谁不知道呢?大家都知道。但是,每当我们讨论文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似乎总是容易忽略它。就目前而论,读者、批评家、媒体对中国文学的现状大多是不满的,话题很多,小说的文化资源问题,小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家的思想能力问题,作家的信仰问题,作家的人文精神问题,作家的想象力问题,本土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问题,作家的乡村写作与城市挑战,作家与底层,图书与市场,作家的立场、情感的倾向,作家与体制的关系,作家的粗鄙化和犬儒主义趣味,还有小说家懂不懂外语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可以说每一个问题都很重要,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让一代作家辛苦一个世纪。可是,我始终觉得,世俗人情这个问题多少被冷落了,我这么说有依据么?有。我的依据就是现在的作品,是我的写作和我的阅读。
中国的小说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小说的进展基本上体现在观念上。观念很重要,尤其是一些大的观念,观念的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小说就不可能是今天这样的局面。现在,我们的小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泛尺度”的年代,人们普遍在抱怨,小说再也没有标准了,什么样的小说是好的呢,什么样的小说是不好的呢,我们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了。可这是好事。由一个强制的、统一的观念,强制的、统一的标准时代进入到现在的“泛尺度”时代,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观念的争论、观念的辨析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泛尺度”或“失度”,它的根子不在今天,而在二十年前。文学没有崩坏,我们只是享受了当年的成果。我们应当为此高兴。至于看小说的人少了,文学没有以前热了,那个原因不在小说的内部,我们可以另作他论。
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在一些观念的问题上,我们当然还要争,还要辩。这是没有止境的。但是,我想说的是,观念的辨析,尤其是一些重要的观念的辨析也误导了我们作家,以为文学,尤其是小说,就是观念。只要站在观念的最前沿,作家就拥有了小说最先进的生产力。就如同我拥有了原子弹,你的手榴弹就再也不是对手了。文学不是这样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