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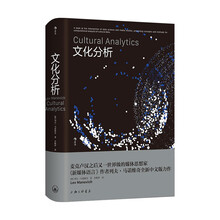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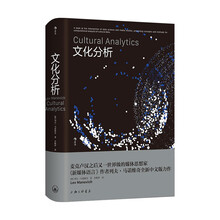






更衣记
——作家怎样给人物穿衣?
1. “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我们读文学作品,遇到书中人物的服饰,无论繁简,恐怕都会一眼溜过去。其实在许多优秀作家那里,给人物穿什么衣服,为何让他(她)们这么穿,而非那么穿,都有讲究。
小说故事性强,描写细腻,涉及衣物服饰更多。小说之外,作家们也会通过戏剧、散文、杂文等文学形式来描绘或探讨衣着打扮这一常见的生活现象。
张爱玲的散文《更衣记》就很别致。它当然不是写某人某次更换衣服的行为,更不是取“更衣”的委婉义之一“如厕”,而是概括地记录了作者所了解的一部分中国人从清末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服饰变迁的历史,即什么时候流行什么衣服。这篇文章提到许多服装款式,光皮衣就有所谓“小毛”“中毛”“大毛”,棉袄的滚边则分“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诸如此类,今天的读者若非专门研究,会觉得很隔膜。好在我这里并不打算专门谈论张爱玲的这篇散文,只是借她这个题目,梳理一下现当代中国文学中有关人物服装的描写。至于衣服上过于琐碎的佩饰,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更衣记》告诉我们,张爱玲对衣着打扮很有研究。她18岁时写的散文《天才梦》结尾那句名言就和衣服有关:“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更衣记》里也不乏这样的“隽语”,比如说,“在政治混乱时期,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中国的服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男子生活虽然比女子更自由,但“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据说张爱玲还跟她的闺蜜炎樱合资办过时装店,自任设计师和广告文案的作者。日常生活中她的许多衣服都自己设计。张爱玲喜欢奇装异服,不怕惊世骇俗。她也喜欢借服装设计来探讨文学理论问题。比如她认为写小说要有“参差对照”,最好是“青绿配桃红”。
现在张爱玲的传记出了好多种,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她究竟如何设计服装,如何像同时代另一位有名的上海女作家苏青所说,喜欢“衣着出位”。但我这里主要还是想说一说张爱玲的小说对人物衣着的描写。
2. 写与不写:张爱玲小说人物的衣着
和《更衣记》一样,张爱玲小说提到的服装款式(包括面料)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也颇为隔膜。《金锁记》里写曹七巧的儿子长白冬天穿“品蓝摹本缎棉袍”,“摹本缎”这种面料20世纪40年代曾流行一时,今天不说普通读者,就是留心服装史的作家恐怕也知者寥寥。我只在汪曾祺1996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小孃孃》里看到过。所以这里也不准备谈张爱玲小说提及的那些过去时代的服装款式与面料,只看她如何通过穿衣打扮的细节来刻画人物。
张爱玲小说人物女性居多。女性通常比男性更注重衣着打扮,所以张爱玲的小说也频频写到女人们的服装。
《鸿鸾禧》写邱玉清马上要嫁给娄大陆,一上来就写大陆的两个妹妹陪着玉清在时装公司试衣服。这两个刻薄的小姑子偷偷取笑未来的嫂子是“白骨精”,又白又瘦。但作者不这么看,她说玉清“至少,穿着长裙长袖的银白的嫁衣,这样严装起来,是很看得过去的,报纸上广告里的所谓‘高尚仕女’”。这一笔并非无的放矢,因为接下来写到,新郎官也认为“玉清的长处在给人一种高贵的感觉”。服装关乎人物的格调,也关乎人物的相互评价。玉清是破落户女子,大陆是暴发户男子。大陆就爱玉清那种格调,包括她的着装风格。
再看《红玫瑰与白玫瑰》,写男主人公佟振保与“红玫瑰”娇蕊、“白玫瑰”孟烟鹂初次相见,就特别强调这两位女主人公衣着上的差异。娇蕊那天碰巧一身浴袍,让佟振保隔着衣服也能看出身体轮廓,“一寸一寸都是活的”,就是今天所谓“性感”“肉感”。孟烟鹂初见佟振保,则“穿着灰地橙红条子的绸衫,可是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笼统的白。”烟鹂很像《红鸾禧》中的玉清,都是“骨感美人”。佟振保一见烟鹂,当场决定娶她为妻。正如他一见裹着浴袍的娇蕊就疯狂地爱上了。娇蕊和烟鹂的衣着打扮,符合佟振保心目中“热烈的情妇”与“圣洁的妻子”的标准。这当然也是张爱玲对暴发户男性的一种典型的讽刺。
有人说张爱玲在服饰上有恋物癖,这恐怕不妥。《红鸾禧》写那两个小姑娘逮着做女傧相的机会,大肆买衣服,恰恰说明张爱玲很警惕女性在服装上的贪婪的占有欲,《红鸾禧》部分内容就是讽刺这种服装上的恋物癖。
不仅如此,张爱玲小说写女性,也并非时时处处都提到衣装服饰。《倾城之恋》自始至终就没有正儿八经写过白流苏、范柳原如何穿衣。白流苏也是破落户女子,离婚多年,住在哥嫂家受气。范柳原是父母非正式结婚生下来的。父亲死后,他好不容易争到继承权,一夜暴富。但因为长期生活在英国,回国后处处不适应,尤其难以克服身份上的尴尬。这就和白流苏同病相怜,但也同病相克,都一样的不信任别人。他们俩的“精神恋”包含太多猜疑和不放心。他们的对话就像林黛玉跟贾宝玉的猜哑谜,或沈从文批评汪曾祺青年时代写人物对话,总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白流苏范柳原彼此试探,机关算尽,哪会关心对方的衣着?人物不关心,作家当然也就没有必要浪费笔墨了。
3. “月白背心”“长衫”“破毡帽”“寿衣”及其他
再看鲁迅。《故乡》写豆腐西施出场,“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除了“没有系裙”这四个字,豆腐西施穿了什么,全无交代。有读者就纳闷:那可是严冬啊,豆腐西施“没有系裙”,却可能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你能看出“圆规”来吗?这或许就是鲁迅描写女性衣着过于简单而惹出的麻烦吧。
再比如《祝福》写祥林嫂:“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完全是神态描写,不涉及衣着。
鲁迅说过,“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鲁迅这里指的是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鲁迅不写祥林嫂衣着,只注重其神情,尤其是“那眼珠间或一轮”,和顾恺之说的是一个道理。
祥林嫂如此,“狂人”、单四嫂子、九斤老太、七斤夫妇、赵太爷、吴妈、小尼姑、吕纬甫、四婶、四叔、四铭、高老夫子、涓生、子君,莫不如此。鲁迅写这些人物,不太关心他们的高矮胖瘦黑白美丑。至于穿着打扮,更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但也不尽然。《祝福》写祥林嫂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做佣人,“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这就凸显了衣着与身体两方面的特征,说明祥林嫂是干干净净守寡的女人。她虽然营养不良,但大体健康,甚至还有某种容易被忽略的青春朝气,而她的衣着也与这种身心状态基本保持一致。
隔了两年,祥林嫂第二个丈夫去世、孩子被狼叼走,不得已再次上鲁四老爷家帮佣,作者也再一次写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强调服饰依旧,说明祥林嫂生活贫寒,几年没添新衣,同时也反衬出她虽然服饰依旧,身心两面却都已判若两人。这就像《故乡》写少年闰土头戴“一顶小毡帽”,中年闰土则是头上“一顶破毡帽”。毡帽相同,闰土却不再是原来的闰土了。
说起毡帽,不能不说说阿Q的打扮。毡帽也是阿Q的“标配”。鲁迅对阿Q的破毡帽念念不忘,十几年之后,有人要把阿Q搬上舞台,鲁迅还特别提醒改编者“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他生怕改编者不知毡帽是什么,特地寄去一个画家朋友所画的头戴破毡帽的几张阿Q的画像。
鲁迅写阿Q,在服装上所作的文章,当然不止一顶破毡帽。比如阿Q和王胡之间的那一场打斗,就起因于他和王胡比赛在“破夹袄”上捉虱子。套用张爱玲的话说,生命对于阿Q王胡可不是什么“华美的袍”。他们只有“破夹袄”,而“爬满了蚤子”则没什么两样。阿Q因吴妈事件被赶出赵府,他给赵府舂米舂热了脱下来的那件“破布衫”也就拿不回来,“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间生下来的孩子的衬尿片,那小半破烂的便都做了吴妈的鞋底”。经过这一次“恋爱的悲剧”,阿Q被赵家和赵家所指使的地保盘剥得一贫如洗,“棉被,毡帽,布衫,早已没有了,其次就卖了棉袄;现在有裤子,却万万不可脱;有破夹袄,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决定卖不出钱”。在“颇有些夏意”的季节,阿Q就穿着仅存的那件“破夹袄”和“万万不可脱”的裤子,仓皇离开未庄。
小说极富戏剧性的转折是中秋过后,重回未庄的阿Q令人刮目相看,而他最大的变化也跟衣服有关。首先是阿Q本人的行头焕然一新,“穿的是新夹袄,看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褡裢,沉钿佃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的弧线”。其次阿Q竟然成了下至邹七嫂上至赵太太都趋之若鹜的各种价廉物美的服装供应商了。等到阿Q把这些货物售罄之后,他的真实身份,“不敢再偷的偷儿”,也就暴露无遗。“恋爱的悲剧”以阿Q的“破布衫”做了吴妈的鞋底告终,“从中兴到末路”这一节,则以阿Q偷来的衣服售完为止。衣服之于阿Q,意义不可谓不大也。
所以如果说鲁迅只对眼睛感兴趣,完全不写人物的服饰,肯定不对。“站着喝酒而穿长衫”,寥寥数字,不就写活了孔乙己吗?再如《孤独者》写魏连殳登场,“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这固然是只写神态,不写衣装。但小说又写到魏连殳死后,只穿“一套皱的短衫裤”,这就暗示他做了官,花钱如流水,却依旧颓废,依旧不修边幅,依旧不为自己打算。
但《孤独者》最后,作者详细描写了怎样给魏连殳穿“寿衣”,“一条土黄的军裤穿上了,嵌着很宽的红条,其次穿上去的是军衣,金闪闪的肩章”。魏连殳就这样“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透过一套“寿衣”来刻画魏连殳一生的颓废,以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真是入木三分。
4. “洋服”的故事
说起鲁迅对服装的研究,不妨再说说他的三篇杂文。
一篇叫《上海的少女》,说“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在以貌取人的上海,别的可以马虎,衣服可马虎不得。鲁迅还发现,女性的时髦漂亮固然能占到不少便宜,但代价是容易被坏男人吃豆腐,“所以凡有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鲁迅观察和分析时尚的两面性,多么睿智!
另一篇《洋服的没落》,内容更加丰富,简直是一段浓缩的服装变迁史。开篇第一句就先声夺人:“几十年来,我们常常恨着自己没有合意的衣服穿”。几十年没有合意的衣服,主要还是政治的原因有以致之。“清朝末年,带些革命色采的英雄不但恨辫子,也恨马褂和袍子,因为这是满洲服。一位老先生到日本去游历,看见那边的服装,高兴的了不得,做了一篇文章登在杂志上,叫作《不图今日重见汉官威仪》。他是赞成恢复古装的。”原来清末民初,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革命党人痛恨满人强加于汉人的那种长袍马褂,而想恢复“汉官威仪”,就是在服装上回到古代汉族文化的正统。但事与愿违,“革命之后,采用的却是洋装,这是因为大家要维新,要便捷,要腰骨笔挺。少年英俊之徒,不但自己必洋装,还厌恶别人穿袍子。”但洋服(西装)的流行,一度竟惹出不小的麻烦,而这麻烦照样还是政治性的,“那时听说竟有人去责问樊山老人(指满清遗老樊增祥),问他为什么要穿满洲的衣裳。樊山回问道:‘你穿的是那里的服饰呢?’少年答道:‘我穿的是外国服。’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国服。’”鲁迅记忆有误,说这话的不是樊增祥,而是另一个文学家王闿运。不管谁说的,西装和长袍马褂的较量,确实牵涉到两种文化的命运。再后来也是政治的缘故,“洋服终于和华人渐渐的反目了,不但袁世凯朝,就定袍子马褂为常礼服,五四运动之后,北京大学要整饬校风,规定制服了,请学生们公议,那议决的也是:袍子和马褂!”为什么有人反对洋装而拥护长袍马褂呢?鲁迅说,“这回的不取洋服的原因却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因其不合于卫生。造化赋给我们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弯曲的,弯腰曲背,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逆来尚须顺受,顺来自然更当顺受了。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违反自然的洋服,于是便渐渐的自然的没落了。”
原来“洋服”流行于中国,有赖于政治力量,其“没落”也因为政治——并非某种行政命令的干预,而是长期政治文化造成的奴才心态起了决定性作用。林语堂提倡中装贬低西服的那篇小品文所谓西装不卫生,本意并非如鲁迅所说“违反自然”,不利于“顺其自然而用之”,即不利于根据身体构造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林语堂确实认真罗列了西装拘束身体而不如中装顺乎自然的诸多细节,并且他也确实言行一致,舍西装而就长衫,倒是惋惜西装“没落”的鲁迅本人并不坚持穿西装,而是和林语堂一样长期穿中装。可见鲁迅本人如何穿衣并不重要,他关心的是服装变迁背后的文化心理。
鲁迅的第三篇杂文,就是他晚年那封著名的书信《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写到“洋服”,以至于牵出经久不息的一段公案。鲁迅说有一次:“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这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两个口号论争”,说来话长。有趣的是当事人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生对“四条汉子”的说法都很委屈,他们都说那天既没在鲁迅面前跳下汽车,也并非“一律洋服”。
但鲁迅偏这么说!大概他觉得什么样的人物,就该有什么样的衣装吧?这还是文学家的思维习惯暗中起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