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冈仁波齐
从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到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底,我除了有两天下到成都去见了个演员之外,整整一年时间基本都待在高原上。
我们车队总共有十一辆车,有六辆是新买的车,从高原上下来后,都跑了四万多公里。从芒康到拉萨,再到冈仁波齐的总长是两千多公里,所以来来回回地不知道跑了多少趟。再加上选景时候走过的路程,这一年真的是围着地球转了一圈多。
虽然我们是在高原上,又要沿着公路拍摄,但我*欣慰的是,整个一年里,剧组没出过任何安全方面的事故。很多地方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戴着安全帽拍摄。有时候正在工作,突然就听到石头哗啦啦往下滚,大家就赶紧找地方躲避,只要被一块石头砸中,人就没了。
我们*发生的意外是,电影全都拍完了,车队从西藏回云南的路上,撞了一头牛,赔了一万多块钱。所以要感谢菩萨保佑,感谢冈仁波齐神山的庇护。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底,电影《冈仁波齐》在冈仁波齐神山杀青,一年的拍摄工作画上了句号。这一年中,好多次经过这里,从四面八方的各个角度,无数次眺望过这座神山,但那都是因为工作,心里想的全是电影的事情。这一次,我终于可以从繁琐的事务中抽身出来,带着索朗尼玛和两个剪辑师,踏踏实实地转一次山。
虽然已经在高原上待了一年,但转山对我们而言依然非常艰难,五十多公里的路程走下来,体力像被掏空了。从海拔五千米的高度往海拔五千七百米的卓玛拉山垭口攀爬时,每走几步路就要停下来喘气,休息一会儿后再往前走。大家就这样安安静静,一步步往前挪动。这个时候谁也帮不了谁,只能心无旁骛,靠着自己的意志坚持下来。
拍片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两个三十多岁的苯教信徒。他们每天都会按照逆时针的方向,围着冈仁波齐反着转一圈,计划是转一千圈。我们到时,他们已经在山脚下住了两年多,转六百多圈了。我们转山用了两天,跟佛教徒的转山方式一样,是按照顺时针的方向走,所以每天都会遇到这两位信徒。大家碰面后打个招呼,然后擦身而过,各自沿着自己的方向前行。他们虽然面容黝黑,衣衫破烂,但眼神里却都是虔诚和执着,我常常被他们的眼神感动。
冈仁波齐是很多教派的神山,大家都为着自己心中的信仰转山。我自己虽然不是一个佛教徒,但我对佛教有亲近感,佛教有很多方法论,帮助一个人去修行,通过这种修行会把内心深处的很多东西看得更明白。
我自己这一路的拍摄,不正是一种修行吗?在电影的道路上,我也是信徒,这一年的拍摄,也是我的一种朝圣—— 电影的朝圣,而我想到达的目的地正是一个导演心中的冈仁波齐—— 一座电影的神山。
就像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所说的,这座电影的神山可能只存在于理想国里,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都是那个完美电影的复制品,只能努力接近,可能永远也无法到达。但我依然要心无旁骛,回到创作的初心,坚定地去寻找心中的神山。
只要是在这朝圣的路上,心里便已是极其幸福的了!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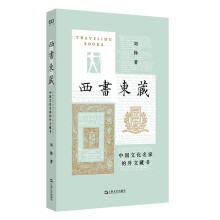








——俞敏洪
这样一个没有折扣的电影,让我特别感动。它是导演张杨作品中,我*喜欢的一部。如果说《爱情麻辣烫》是从窗户向外张望着世界,那么《落叶归根》是拿一个相机记录着一路的风景,《昨天》是一面镜子,让你正视自己的内心,《冈仁波齐》是一面圣洁的湖水,照着天,映着人,让你看到这个世界的一切。
¬——史航
自然温和扎实而且没觉得闷。没有局也不自说自话。被感动到了。好电影。朴素自然,心生敬意。
¬——朴树
对于像我这样的城市人来说,我想可能要下很大的决心才能义无反顾走上朝圣之路,这也是我来看《冈仁波齐》的原因,想找到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的一个答案。
——老狼
这样一部没有任何明星的纪录风格的文艺片,六天突破一千六百万票房,说明我们的市场和观众开始多元化了!导演采取了一种纪录-戏剧Docu-Drama的样式,让我们近距离地接近和感受了一次藏民族的文化与精神,实属可贵!我在西藏拍过两部电影,知道张杨导演要花多大的力量、吃多少苦才能拍得这么好,这么深入。从这点讲,怎么夸奖都是不过分的。”
——谢飞
朝圣路上的行人,身上令人动容不是命运里的人如何搏斗挣扎,而是人的接受,人的低首伏耳,人从容慷慨地拥抱了命运里的每个时刻。所以,《冈仁波齐》也许不是一个西藏故事,它是人类的故事。他们的行进和休憩和他们经过的四季,即是一个人类生活的缩影,无可避免,无法逃避,但无论遇到什么,山仍然会在那儿,而他们终将到达。
——鞠白玉
早年在西藏拍过戏,看张杨导演的《冈仁波齐》,仿佛还能感到高原冷冽刺骨的风。漫漫朝圣路,唯信仰给人力量,让人无惧生老病死,从平凡中也能生出伟大。值得一看!”
——李冰冰
电影*正常的生态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是谁愿意看什么电影就有什么电影可看,可我们现在除了小鲜肉的观众以外,别的电影类型已经基本死亡了,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状态。《冈仁波齐》这样的电影,在目前的中国影坛中非常罕见,还有人在坚持这样去做,把它作为反映社会真实的一个影片,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尊重。
——芦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