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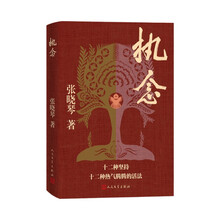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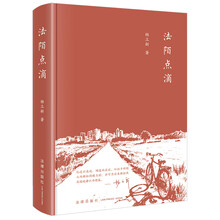
☆在图书内容层面的复制变得愈来愈容易的今天,一本有阅读价值的书可以化身千万,不再稀缺。但读书的人在其上面留下的痕迹,才是使一本书变得有个性、变得独一无二、变得富于意味的决定因素。
☆过去对于阅读史的研究,往往只以文人学者自己的著作、文章、信札或日记为主要史料,未能落实到“实物”的层面上。本书专门对那些真的被人翻阅过的书进行考察,以期窥见阅读的真相。实物带来的震撼,远远超过语言叙述。
☆本书着重考察民国时代中国知识分子阅读西文书的风气,包括哪些西文书是中国读者曾接触过的,又有哪些书是流传甚广、读者甚众的。这种“知识的考掘”的过程,意在挖掘思想、观念、知识的脉络,实有深刻的意义。
☆“书自有其命运”,有其遇与不遇,直至它找到能领悟其意义的读者。在炮火战乱、赀财俗务、爱恨嗔痴之外,尚有一小片安静可在书里觅得。翻开书页,读书人将为前辈学者治学之精勤所打动、所感染,亦当因此而有异代相知之感。
☆要享受淘书乐趣,仅凭运气远远不够。在旧书网站的浩瀚图海中坚持浏览到最后,方能领略其中的无限惊喜。在经验和运气综合作用之下,培养起提防作伪的意识和识破作伪的本事,买到可宝贵的书籍,这份乐趣,唯有亲身经历方能体会。
☆在写法上,本书采取“书话”的方式,不故作高深;着重事实的讲述,谨守实证的边界,不做理论的推阐。作者用严谨的态度,精心进行材料的积累和甄别工作,力求为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生动的阅读世界。
《西书东藏:中国文化名家的外文藏书》记述中国现代37位著名学者、作家、文化人曾经读过、收藏过的西文书,这些书后来又都成为作者的收藏。在中国,对古籍的研究、书写自来多矣,而对近代以来境内流传的外文书的研究,还没有过如本书这样的作品。作者选取的37位中国文化名家,第一位是1912年时35岁即被擢升为外交部次长的颜惠庆,最后一位是1949年时28岁正在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夏志清,他们均是在1912年至1949年这一时段中有过重要经历的知识分子。
作者细心钩稽书背后的历史,依据实物讲述名家的阅读和藏书故事,做“知识的考掘”,意在挖掘思想、观念、知识的脉络,实有思想层面深刻的意义。在写法上,本书采取“书话”的方式,不故作高深;着重事实的讲述,谨守实证的边界,不做理论的推阐。随书附入大量书影,可供读者参考和鉴赏。
一
现代中国战乱、变动频仍,民众保存文献图籍的意识也较淡漠,得到相对完整保存的私人藏书少之又少,因而针对具体人物的藏书进行研究难度很大。若不将藏书家们有心纂辑的藏书志计算在内,现代著名的文人学者中,只有梁启超、鲁迅、胡适等寥寥几位在身后有藏书目录的出版。在考察名家西文藏书方面,近些年做了最切实工作的,当数周运的长文《知堂藏书聚散考》以及《乘雁集》中的其他几篇同类文字。此外如徐亚娟《国家图书馆藏褐木庐藏书珍本举要》(收入《文津学志》第四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11月版)、马鸣谦《施蛰存外文藏书摭谈》(《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0年10月10日)等亦有价值,而像冯佳在其专著中对何其芳的西文藏书进行了分类统计却未详加描述,则不免让人引为遗憾(《中国近现代作家与藏书文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版)。总的来看,对名家西文藏书的研究是稀少而相对薄弱的,或许也因为学术界对此类研究的价值未必推崇。
《西书东藏》中谈到的书,有不少是只有名家钤印而无题识的,传统的版本目录学家对这样的书通常不屑一顾,除非是黄荛圃之流的旧藏。晚近风气稍稍起了变化,一些图书馆的著录也开始留心藏印的细节。我的见解或与许多人不同:在我看来,未来恐怕只有书上留有阅读者痕迹的书才值得收藏。而那些既没有题识、批注,又没有钤印、签名的书,哪怕印量不多,存世有限,也不值得普通人费心搜求庋藏了。这是因为数字技术正在使图书内容层面的复制变得愈来愈容易,一本有阅读价值的书,借助方便的复制手段,可化身千万,由稀缺变得不再稀缺。本身贵重的书,其物质形态存贮于图书馆或文献机构就够了,其电子化身则将通过网络飞入寻常百姓家。而人留下的痕迹,才是使一本书变得有个性、变得独一无二、变得富于意味的真正的决定因素。随着搜集、收藏和相关书写的展开,我的这一认识逐渐明晰起来、稳固下来。
现今的史学领域和文学领域都有学者从事“阅读史”的研究,这些研究往往只以文人学者自己的著作、文章、信札或日记为主要史料,却极少能落实到“实物研究”的层面上。没研究过实物,想真切地把握实态是困难的。我以为,只有对那些真的为读者所翻阅的书进行考察,才能窥见阅读的真相。让我们选取《西书东藏》里的两个例子来说明:汪荣宝藏卢梭《忏悔录》,很多书页书口未裁开;赵萝蕤藏瓦莱里《杂俎五集》正文从第二页起即未裁,巴尔扎克《贝姨》也只裁到第33页。二战以前法文书普遍采用的这种毛边形态,像一段记录读者阅读真实进程的监控录像。我们不能下判断说,一本书已裁的部分裁书人就一定读过,但我们完全有把握说,一本书未裁的部分裁书人一定没读过。由此,我们通过实物考察,得出了如下结论:汪荣宝、赵萝蕤未能认真阅读他们的藏书。试想,假若汪荣宝曾在日记里记下购《忏悔录》一事,假若赵萝蕤有记书账的习惯,而其中就有《杂俎五集》和《贝姨》的记录,那会不会便有研究者以为他们真读过这些书,并由此出发,对他们的观念形成与思想构造展开论说?“实物研究”,可以让研究者避免上述的这类尴尬,还可以让他们看到仅靠文字记述绝想象不出的具体阅读场景。《西书东藏》以图文并重的形式展现了洪业、周一良、王锺翰等学者学习外语、研读语言学著作时的孜孜矻矻,尤其是周一良读《语言及诸语言》,画线、批注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全书总页数为436页,其中354页有周一良的画线、批注。实物带来的震撼,远远超过语言叙述所能起到的作用,我相信,只要读者看过书中展示的有限的几张图片,便很难无动于衷。真正的阅读史,就存在于从未裁开的书页与密密麻麻的批注的张力中。
二
在中国做西学的“阅读史”研究,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考察某一时代的阅读风气,包括哪些西文书是中国读者曾接触过的,又有哪些书是流传甚广、读者甚众的。
我在此举一个书中未述及的例子。比如,你要考察蒙森(Theodor Mommsen)的名著《罗马史》(Römische Geschichte)在民国时期的接受史,在各类报刊数据库里更换关键词反复检索,也未必能得到几笔资料。2023年9月,我得到一部1927年柏林印的德文版《罗马史》第五卷,在书名页左下角钤一长方形朱文篆印——“梁颖文赵懋华藏书之印”。赵懋华女士,现在知道的人已不多了,她是北京大学最早的九名女生之一,后往德国深造,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德文的博士论文《叔本华学派的伦理学》曾获贺麟先生赞许。1934年贺麟撰长文《从叔本华到尼采》专门评介此书。赵女士的丈夫梁颖文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秘书长、财政部次长。书名页右上角的签名当是赵懋华女士留下的。这对履历不凡、学养殊深的夫妇购藏的《罗马史》,是不是中国的蒙森接受史上一个强有力的音符呢?
同一种西文书,有多人读过,这一现象在我的收藏中亦有所体现。比如,《西书东藏》里写了周作人旧藏的1903年版《节本希英字典》,后来我买到过1899年版,为哲学史家石峻旧藏。在网上还见过1892年版,为翻译家王智量旧藏。说明这部小型的希腊文字典很受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
我曾在2017年3月发表的《另一种“知识的考掘”——丙申所得名家旧藏外文书小记》中提出,对西文书在中国的传布进行研究,实有思想史的意义:“往大里说,我觉得这有点像是一种最边缘的思想史的工作,让我们留意到这些名家曾读过什么、有怎样的视野。或者说,这是另一个层面上的‘知识的考掘’(l'archéologie du savoir),挖掘思想、观念、知识的矿脉、水脉,一直挖到最细末的支脉里去。”这里借用了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概念。我相信《西书东藏》提供的材料将有助于读者进一步做这方面的知识掘进。
考察《西书东藏》述及的几十种西文书的购买及阅读地点,或许就是一个有趣也有启发性的题目。让我们先看看下面的名单:
美国麻省剑桥:唐钺 浦薛凤 周一良 王锺翰
美国俄亥俄州特拉华:洪业
美国芝加哥:赵萝蕤
英国牛津:向达
德国波恩:姚从吾
奥地利维也纳:李一氓
瑞士日内瓦:乔冠华
印度孟买:杨刚
此个名单只列出了部分明确可考的国外购书地点和相应的购书者,但仅仅是这样简单的罗列,就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种书籍文化的拓扑结构,一份全球知识流动的地形图。
如着眼于阅读者的身份,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时间维度上的比较。如《西书东藏》开篇的两个人,颜惠庆、汪荣宝,他们是从晚清跨到民国的外交界人物;而后面写到的李一氓、乔冠华,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红色外交家。比较这两组人在选书、阅读上的趣味差异,无疑是有意思的。李一氓在维也纳大搜马、恩著作的初版本,乔冠华在日内瓦第三次读马、恩书信选集,这样的爱好,恐非颜人骏、汪衮父辈所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