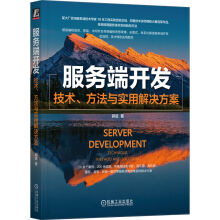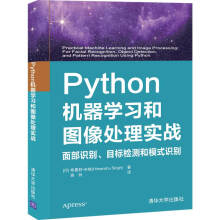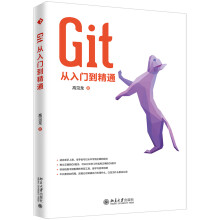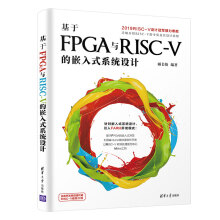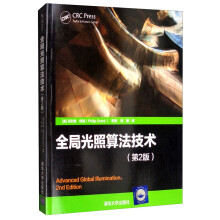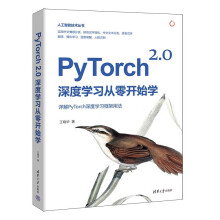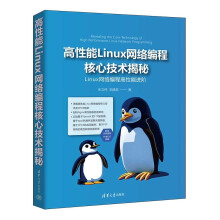迟子建是要他们永远穿上奇装异服,装疯卖傻,做我们的“风景”啊。鄂伦春人怎么就变成了“他们”?“我们”是谁?“我们”凭什么把鄂伦春人风景化?风景化的动力机制,就是“我们”的倨傲和无知。
迟子建有篇小说叫做《音乐与画册里的生活》。这个题目倒能恰当形容迟子建的复制写作——她一再演绎的压抑和拯救的“神话”,悉心勾描的异域风情画面,都是由通俗音乐(比如乡村民谣)、旅行画册和流行读物提供的现成生活啊,哪些是她自己的?
三、没有历史,哪来日常?
复制也指对于自身写作模式的一再克隆。苏童说:“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褒扬也可以从背面读:一个作家怎么能写了二十多年还是一个调子,一种模式?世事改天换地的迁移,生命水滴石穿的变化,怎么就渗透不进她的写作?
迟子建的写作模式就是先铺叙人与人之间的误会、伤害,最后让大家在一种不期而至的契机中谅解、拥抱,生之温情和诗意于是汩汩不息。《驼梁》通过高考落榜生王平的坎坷心路告诉人们,世界再幽暗、寒冷都不要紧,一直朝前走,到了驼梁,就会满眼春色了。《驼梁》实在是迟子建创作世界的元叙事——她所有的作品都欲扬先抑,让我们在跌跌撞撞中直抵驼梁。站在驼梁回望来路,辛酸也显得楚楚动人,不可或缺,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我”所想的:“真正的喜悦是透露着悲凉的。”于是,《白银那》的结尾,乡长一定会原谅马占军夫妇,因为“他们也是咱白银那的人,我相信他们以后会变的——”《日落碗窑》里,关老爷子一定会烧出一只完美无瑕的碗,“仿佛是由夕阳烧成的”,刘玉香也会平安产下一个七斤半的男婴。《鸭如花》一定会让一只白褐色的鸭子在逃犯的坟头开成一朵美极了的花。《第三地晚餐》中,马每文和陈青一定会回到大卧室,相拥而眠,陈青用金黄色丝线连缀睡衣上的裂口,竞有种惊人的美丽,“既像从天边飞来的一缕晚霞,又像一株摇曳在紫花丛中的黄熟了的麦穗”。《越过云层的晴朗》中,“我”在弥留之际一定会想:“我马上要越过云层,去拥抱它背后的太阳了。那里始终如一的晴朗,一定会给我一种住在暖屋子的感觉。”《伪满洲国》更会让破镜重圆,“那铜镜上被斩断的花枝又连在了一起,那阻隔了的云彩又飞涌到了一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迟子建文学世界中调子最阴郁的一篇,蒋百嫂一声“这世界上的夜晚怎么这么黑啊”,是她笔下最凄厉的绝叫。迟子建一定会在小说结尾勉为其难地消解掉苦难:“我突然觉得自己所经历的生活变故是那么那么的轻,轻得就像月亮旁丝丝缕缕的浮云”,世界仍旧是爱的翔舞。不用多举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迟子建的小说都是对于那个元叙事的复制。问题是,我们真的能够抵达驼梁吗?或许,驼梁压根就不存在?没有的话,只好生造了。于是,迟子建笔下的转机往往来得十分突兀,由转机带来的诗意也不可避免地显得苍白、做作。她曾在《晚风中眺望彼岸》一文中说:“现在我不太喜欢屠格涅夫了,因为他笔下的悲剧人为的痕迹太浓,而且弥漫在作品表层的诗意氛围太明显。”如果把屠格涅夫换成迟子建自己,这段话倒是恰如其分的自评。我想,迟子建要是有自省精神的话,应该不太喜欢自己。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