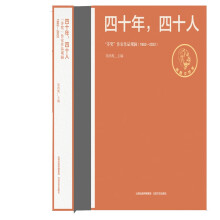他对形象思维的界定只是用否定式的排除法来缩小其外延,诗有别材,非关书也、非关理也。但是诗“关”什么呢?他并没有直说,也并没有科学地揭示这一内涵。因此,我认为严羽“约略体会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区别,并用否定式的排除法缩小了它的外延,但他找了一个十分有特色的概念来表示这种朦胧的认识,这一概念就是“妙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
李泽厚先生也有同感,他说:“形象思维本是一个老问题,这个词虽然出现较晚,但问题很早就被注意和提到,在宋代而不满意宋诗,以盛唐气象作为诗的最高境界的著名的《沧浪诗话》便曾突出地提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又说‘盛唐诸公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就是说,诗有不同于读书、说理的自己的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概念、语言或思维(言筌、理路),而要求在有限的言词形象中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和意味,这是针对当时宋人以议论为诗,在诗中大掉书袋,比兴缺如,弄得形象干瘪、意兴索然而发的。”从郭绍虞和李泽厚先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都认为严羽在《诗辨》中发现了形象思维问题,从严羽自己的表述看,他得到这一发现后非常喜悦,令他喜悦的原因是他发现的这一领域是一个非常新鲜、重要的天地。
艺术要表达情感,诗要言志,言志不是空说道理,不是让诗成为政治的传声筒,而是要用形象,这一问题古人很早就发现了,并用“象”、“象外之象”、“兴象”、“意象”等概念来描述它。同时,运用语言塑造形象的方法和技巧,即形象化的方法也非常成熟,如比兴、隐秀、声律、夸饰等,但是对于综合运用形象化的方法创造“兴象”的思维活动的认识却十分简陋,、严羽的诗歌理论正是发现了创造“兴象”的认识活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