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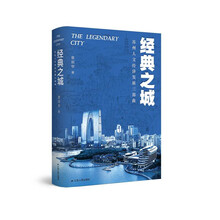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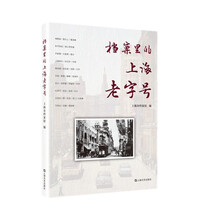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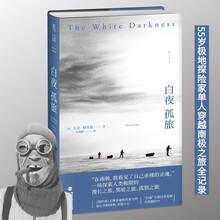
编辑推荐1:2014年英国《每日电讯报》年度好书
杰奎琳.罗斯慎重而坚定的思考得到《金融时报》《独立报》《先驱报》《文学评论》《弗里兹》等多家报纸和书评人鼎力推荐。
编辑推荐2:致敬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
《黑暗时代的她们》书名源自汉娜.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是作者杰奎琳.罗斯对其致敬之作,由充满智慧的女性的人物素描所构成,作者想要向读者表明和传达的主题和阿伦特相似: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女人,源于她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编辑推荐3:我活在这个世界,可这个世界不属于我。
我们生活在一个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女性的侵犯与歧视已经有所收敛的时代。这个世界距离倾听来自女性的声音究竟还有多远?
更多精彩好书:
《黑暗时代的她们》以历史上三位女性开篇(富有革命精神的社会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受到家庭悲剧和纳粹迫害的德国犹太画家夏洛特.塞洛蒙,电影偶像以及大众的消费对象玛丽莲.梦露),她们的经历讲述了如何通过戏剧性的事件在上个世纪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将不可说之事带入光亮之下。
同时,《黑暗时代的她们》也关注当下女性,分析多起臭名昭著的“荣誉谋杀”案件,讨论三位在黑暗的角落里滋生出优秀作品的当代艺术家——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耶尔.芭塔娜、泰蕾莎.奥尔顿。
《黑暗时代的她们》是一本兼具文学性和心理分析风格的佳作,学术思考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向我们展示了这些充满智慧的女性是如何为女性主义创造一个新的模板。
我们的讨论,看似偏离所谓“关于女性的常识”太远。我意识到,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女性,绝不是本书中的形象。人们通常更习惯于把女人看成情绪的动物,并且无法像男人一样游刃有余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自然,“女性主义”也因此充满了过多的非理性诉求。或许,这种状况并非自发形成,而恰恰是由于鼓吹“自由”理念的西方社会自己强加得来的。对于每个人来说,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这都是个焦点话题。譬如在伦敦,谈论女性所要求的平等,就是一项挑战,尽管人们很容易就给出肯定的答复。一份署名为“西伦敦标志”的来信寄给了当地的《都市日报》,上面说“我实在想知道女权主义到底在说什么,如果不是非要有这样一个称呼,她们完全可以称呼这种要求为‘女性平等’”。写这封信的人进一步补充道,“也许,人们只是不愿意为这样看上去简单的概念来背书,才草草表示自己的支持。”他提出的这种不安,并非女权主义的本意,却成了当下现实里的氛围。《都市日报》则为这封来信拟订了“女权主义以其他名义出现是一份值得庆祝的事业”。
正如刚刚我们被告知的,女性主义应当戴上面具,假装成别的事情(即“其他名义下的女权主义”)。“玫瑰不叫玫瑰,依然芳香如故。”如果这句著名的谚语可以在此得到所谓佐证,那也许仍是件未被察觉的行为——女性主义的“芬芳”尚未得到承认。另一句可以引用在这里的谚语是“爱是不可名状之物”,这是一种微妙的,但也不那么微妙的同性之恋的暗示。以女同性恋的缘由来拒斥女性主义,像是说“那一群同性恋”,正是反女权主义者的另一种策略。女权主义令许多男人们——其实不只是男人,感到沮丧。它煽动了事物的纷扰,动摇了我们的心灵。像是一个丑陋的斑点、血浸透的纸张、班柯的筵席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的典故,无辜的班柯在筵席上被麦克白刺死。——译者注。就好像女权主义成了人们生活中极端难处理状况的代表:它代表了隐秘的心灵、身体、暴力、性爱与死亡。它总会唤醒这些词汇一同出场(就像是语义学上的“姐妹关系”)。不像是“女性平等”,女权主义让女性的温柔与本性相结合,尤其是后者,暗示了一种动物性的基本文明,而这种文明又恰恰是西方文明宣称意欲提供保护的。由于女性主义在女性生存权利上的不知悔改,她们在这一问题上便与男性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至于进一步激化成了政治性的危险运动。但女性主义和女性自身一样,始终被以非理性的眼光看待。它似乎意味着一种教条与力量的双重灌输,同时肩负起抢掠世界、造成不安、夸大女性遭受的暴力的任务。人们始终坚持的是现行的角色分配是有效的。倘若不是,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疯狂而失序,任何人都可以去探看和观察:从性生活的角度来看,许多非理性的生活中,那些非理性的人,仍然会遵循上个世纪保留下来的疯狂可笑的习惯。但我们今天仍承受这些本可不必承受的伤痛。因此女性主义应当提醒人们关于世界的无理性判断。但在本书中,这些女人同样还在坚持,并尝试去一一回应所谓正统社会的质疑与问询,而她们同样可能遭受欺骗,蒙受危险。
只需随意找来一张报纸,我们便不难目睹这个世界对女性的苛刻——2013年7月的解放广场,响应革命号召上街游行的女孩们,却遭到武装人员的包围和强奸。在强奸她们之前,暴徒让她们围成了一个圈,然后剥去了她们的衣服。和许多性暴力一样,羞辱才是真正的目标(针对女性的暴力尽管被明令禁止,但却是必须要做的事)。女人们称之为“地狱之环”。治安维持会的救援者,带着刀与火焰喷射器,轮奸了他们被要求保护的对象。一个伊朗女人,完成了身着全副伊斯兰服装泅渡里海的壮举,只是因为作为一个伊斯兰女人,她不能公开露出属于自己的身体。在稍早被禁止的公开水域项目里,她还遭到了巡警的驱逐。这看起来是女性因为自己的身体遭到了惩罚,实则是她本身的存在便意味着一种冒犯。在同一个版面上,两个沙特阿拉伯妇女面临牢狱之灾,因为一个加拿大裔妇女被囚禁在自己的家里,她向她们求助,而她们只是为她和她的孩子们投递了食物。判决声称她们的罪过是“未经丈夫许可,擅自帮助他的妻子”。这两名女子先前都曾被卷入到女权相关的事件中,其中的一个违抗法令公开驾车,还将视频上传到了视频网站上(之所以禁止女性开车,是因为当地普遍认为开车会损害女性的子宫,而作为回应,她发起了“女性驾车日”的活动)。
在同一个星期,有两个从事出版业的英国女孩被报道离职。她们中的一个是自愿的,而另一个似乎是受到了排挤。稍早的时候,WH史密斯公司的女老板下台,而六个月前,培生集团与企鹅公司里发生了同样的事。这些女人都是被男人取代的。而在相邻的版面上,报道称伟大的女性社会活动家伊丽莎白·弗莱伊(Elizabeth Fry)在5英镑纸币上的位置,将被温斯顿·丘吉尔取代。而在抗议之后,相关部门则在另一张纸币上妥协,宣布10英镑上的人像将更换成简·奥斯汀。这看似是女权运动的一次胜利,但其实是卡洛琳·克里亚多·佩雷兹(Caroline Criado-Perez)通过并不光彩的示威要挟才得以实现的。英国版《VOGUE》的前编辑科斯蒂·克莱门茨(Kirstie Clements)曾将女性的身体比作今天时尚的机器。女孩子们时常要在自己的胸部“大做文章”。而高跟鞋则让她们显得纤细,却有些站立不稳。一个看起来奄奄一息的模特,俯卧在喷泉旁,留下了最后一张人们称之为时尚的摄影。归根结底,她们只是一道供男人欣赏的风景。
这些故事是不同的,虽然在它们发生的这些年里,你都可以从每周的新闻中选出相似的故事来替代。关于5英镑纸币和出版业女孩们的退场,可以视为对女权主义运动自以为成功的反驳(在职场这种例子正在增加)。但因为要去回应发生在解放广场或沙特阿拉伯的可怕事件,我们必须坚持在西方,女人们是要更加自由的,所以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国家才不会发生。就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关于年轻女孩的性虐丑闻报道,在英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某些邪恶正在不断滋生。吉米·萨维尔英国已故知名主持人,死后陷入性侵未成年少女丑闻。——译者注(Jimmy Savile)事件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我们知道,他不过是充满虐待、暴力、欺侮、忽视与忍耐的娱乐文化版图中的一块,尽管他古怪的举止会让人们把事件归结成一个疯子的作为。当萨维尔的事情败露时,上百个受害者站了出来,只有在此时她们才肯说出自己曾经遭受的一切(即使一些女人的证词由于时日过久并未成为呈堂证供,但创伤与讲述之间的精神分析仍然是十分棘手的课题)。2013年春天和夏天,在英国和美国,有关未成年少女被虐待的新闻同时覆盖了很多报纸的版面,这是我们很难无视的事情。在威尔士,五岁的小女孩艾波尔·琼斯(Apirl Jones)被她的邻居马克·布里杰(Mark Bridger)谋杀。而在英国,十二岁的蒂亚·夏普(Tia Sharp)则死于外祖母的朋友斯图尔特·黑兹尔(Stuart Hazell)之手。对此我们务必要当心。这些故事无疑是令人痛心的。2007年的联合国妇女代表大会上,一项统计数据显示,超半数的劳动妇女并没能享有合法权益。而相同比例的女性也无法在家庭暴力中得到有效庇护,性犯罪更成了现代社会最显著的暴力行为。在2013年的国际妇女节上,包括人权律师海伦娜·肯尼迪、菲利普·桑兹,以及歌手安妮·兰尼克斯在内的五十位代表,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发布在英国《卫报》上的公开信声明,“从十五岁到四十四岁的女性,她们的生命由于暴力侵犯、家庭暴力所遭受的威胁,要远超疾病、车祸及战争。”
一年之后,2014年4月,家庭暴力、破坏女性生殖器和强奸被当成战争的武器——现在被称为犯罪战争,跃入公众视线中。十七岁的女学生法赫玛·默罕默德在公众面前说出了女性割礼的真相,并受到了英国政府的关注,联合国秘书长也亲自聆听了她的演说。而在阿富汗,在上学途中被塔利班分子流弹击中的女孩马拉拉·尤萨夫扎伊则向全世界表明,如果可以坚持为女性实现她们受教育的权利(“使她们成为人”,有人这样概括),那些压迫她们的暴力终有一天可以完全解脱。但这些可怕的事情并不能被等量齐观。而无论是将它们进行归纳还是区分,我们都应当有一套稳定的手段使其中的罪恶得到清算。我们也可以只是期望政策可以得到改变,在英国可以有治安措施来针对家庭暴力,有教育手段规避割礼的发生,由国际法庭来清算战争期间发生的强奸行为。但事实上,这些由女性讲述的事件,绝大多数还是被忽略和隐藏起来了。但即便如此,这也是值得被记录的。在本书中我们不止一次提到的女性,例如罗莎·卢森堡,对自己所介入的公共领域始终不曾放弃怀有憎恨。这或多或少无关于她们所谈论的内容(虽然成为一个革命者并无益于得到救赎)。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死去的女孩,也会遭到恶意的揣测(莎菲莉亚事件)。而其他的女孩,像法蒂玛·萨西达,在介入公共类领域时要承受的风险显而易见。我们可以说,像法赫玛和马拉拉这样的女孩,她们遵循的是这样一条道路:她们不只是说出了世界不希望从女人口中听到的话,她们还大胆地以不怀任何歉意的表现,向世界说出了真相。
可女人对于说出这个病态世界的真相,终究拥有自己的义务。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女权主义者来说,我们应当反对对男性世界的丑化,也不应过分谴责包括女性在内的这个社会,使它的基本框架摇摇欲坠。我们应当假定,男人永远是男人,那些睾丸素作祟的行为,尽管千百年来始终被争论不休,但终究是他们为何并且始终会呈现的状态。这是最基本的事实,即使女权主义的任务真正得以完成,男人和女人最理想的状态,仍是各司其职。波伏娃已经指出,女性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塑造成的。她使得性别认知进入了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一种需要男性许可的身份。这似乎是一种十分古怪的场景:男人是“纯生物”的,而女人却是“纯文化”的。这展示了一种陈词滥调:女性是肉体的王国,无限趋近于自然,而男性则是外化的世界,是公共的核心,是社会的生命所在。这在当下处于经济低迷期的英国,得到了毫无遮拦的回应。可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这无疑只是个借口。
我们还可以总结,女性所遭受的欺压,其根源在于男性感到自己的男子气概受到威胁。于是针对女性的侮辱,往往发生在男人失败或无限贫苦之时。这个问题使我们来到了一个相对困难的路径上。这似乎是在说,当男性向女性施加暴力,就意味着他的男性认定得到了补偿,可这同时也证明了他的软弱。正如在《黑夜的另一张脸》(The Hidden Face of Eve)中,纳瓦尔·萨达维(Nawal Saadawi)描述了阿拉伯男人(尽管她很乐意把自己的学说推广到所有男人身上)并不能忍受一个聪明的女人,因为“她会看穿男人主宰一切的男子气概并不真实,并不是基本的真理”。所谓的男子气概,不过是原始的武器和自欺欺人的把戏。就像是在露天游乐场里的碰碰车——再多这样的勇气也不会使得车毁人亡。不断声张男子气概毫无意义——但越是无意义,男人们就越是会去强调。
在多数令人不安的矛盾里,性别差异被认为是发生暴力的原始动力。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女权运动会突然爆发,它取得的结果与所付出的努力并不相称,为何人们还会投身其中。当然我们并不需要再去强调相关的生物或是文化证据。事实上,最终的原因应当归结到黑暗且不易理解的、二者的中间地带。我始终强调的是,这世界恐怕终究是一个没有理性的地方,男人与女人寓居其中,时时刻刻都可以为自己的恨意和暴力找到能量来源。当男人看到女人,他们在想些什么呢?精神分析或许可以表明,他们所面临的威胁,不会比面临自己的时候少。在汉娜·阿伦特看来,置身于现代简单的差异理论是难以处理的,却可以解释暴力的根源。剥夺国籍,使他或她成为无国籍之人,在20世纪是一个诅咒,因为那意味着一个人将永远流离失所。她“仅仅由于不同而处于永远的黑暗之中”,只得飘荡在湿冷而虚弱的国家之中。这是一个“男人永远无法改变和有所作为,于是只得尝试推翻毁灭”的领域。我们再一次介入了一个直接的悖论形式:对人类力量的试炼,最终却导致了人的羸弱。
阿伦特的重点并不在于女性被憎恨,但她关于差异的探讨,实际上使得关于女性遭遇的讨论有了新的可能。“人的性别意识是一种固有的创伤,”精神分析学家乔伊斯·麦克杜格尔在1996年开始了自己的专题研究“爱欲的多张面孔”。性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为它是一种无法被控制的力量,同时它也是一个未知的领域、渴望被破除的禁区,但人自己却永远无法抵达真相。这是一个所谓的知识也“支支吾吾”,永远要面临自身局限的场所。在英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梅勒妮·克莱因看来,两性间本身就存在严重的比例失当(我们长期以来都在以男女匹配的契合为由嘲笑那些同性恋者)。男孩会放弃自己的身份认知,而女人则在一出生,就无限接近于母体,接近于自己性别的真相。男孩和女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长大并面对这个世界。克莱因并没有因她的社会评论而享有声誉,但这个有趣的评论却把我们引向了另一个侧面。她认为这可以解释为何男性在和女性竞争时,“更显自私,尤其和他与其他男同事竞争时相比”。成为女性,本身就是一种男孩身上洗脱不掉的烙印,因为他本就来自母体。对于男性而言,探索自己的身体,从拒绝到接纳,是他长大成人的必经之路。而对于女孩,无论她未来将面对怎样复杂的身份认定,也无所谓她将走上一条怎样复杂的性别之路——按照精神分析的说法,即便是通常意义上的“正常”,也意味着并不容易的身份认知——她都会很容易认出自己,从容地完成安置或替换。这意味着,成为女性的过程里,她并不必经受“拒绝”。
与女性的竞争,是男性更习惯乐于忘却的认知。他和男人的竞争尽管很可怕——战争、政治斗争,或者只是在更衣室的“比较大小”,都是可以用更文明的方式来取代的行为。而在上述理论里,男性对女性的攻击,也就并非出于本能,而是由于他们从根本上会将女性看成鬼魅一般的提醒者,提醒自己“作为女性的过去”和男性之名的虚妄,而那显然是他无法承受的。“荣誉并不只是女人要保持原样才能活命的东西,同时也是男人着力捍卫,以免在女人面前丧失尊严的东西。”阿布巫达如此谈论道。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攻击,并不只是因为他没能成为她的控制者,而同时还因为她曾是,并且现在可能还是拒绝他的人。关键是克莱因的“竞争”,它意味着男女固然不同,但却十分相像。这就是为什么在最初,性别的契合会令人感到满足。但时日愈久,这种“正常”便会被最初身居下位的性冲动取代,使之成为世界性的需求。
当然这并不寻常,而是基于深入的精神分析得出的非一般性结论。必然的性别认知并不会耗尽我们的可能性以及一个人全部的内在诉求。也不是所有男性会面临以上的困局,或许只有解放广场上的暴徒们才会如此。不是所有男人都在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的性别。但没有一种暴力会比它更加致命和容易失控,因为当你尚未搞清它如何发生,便可能已经身处其中,结果就是必然的坐实。男人无法看到自身身份上的欺骗性,精神分析会为所有盲目的自信找到根源,毕竟它的发生是如此的艰难和迅速。而女人又太容易被诸如残渣、胞衣而吸引,成为一种无法控制和知晓的世界与心灵:那正是阿伦特所说的“男人永远无法改变和有所作为,于是只得尝试推翻毁灭”的领域。同时她也认为,那无法控制的凌乱和由于新生和新开始而导致的不可预测的时刻,也正是女性召唤而来的内容。无论是否成为母亲,女人都有这样一重身份认定。这正是本书一开始交代的内容。“没有逻辑,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将会使强权的运转呈现尽可能多的可能。这是因为对于所谓的逻辑之链而言,它的开端往往只是以假设作为前提和形式。”这同样解释了为何极权主义总会与对血统和生育的控制相伴,因为恐惧的制造者“唯恐人们在世界上建立起超出他们控制的联系,从而提高他们自己在世界上的声音”。对于这样的世界我们无从控制,因此只好试着进行毁灭。而本书中的女性却无意控制世界,她们也不曾为非正义的命运而奋战。把握自己的生命,已经是她们抗争的核心了。
让女权置于我们的文化之中,将会质询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有关我们所认可的当代社会的角色分配是否合理。那实际上是一种傲慢的控制、一种在自己的领域内无情而残忍的信仰,宣判世界将会被不确定性包围。令女权主义置于内心中承受最多痛苦的位置,并不需要让它从闪光灯下退场,仅仅是因为在我们鲁莽地抗议时,却让这些思考本身沦为“卑微的侍女”。让我们回顾本书的第一段引文,它来自卢森堡写给约吉谢斯的信:“你可以想象,我对新生活的全部勇气,恰恰来自于那些对我灵魂的伤害。”此时刚刚抵达柏林的卢森堡,正被“完全的陌生和全部的孤独”包围。而她决心在这座城市的政治领域留下自己的标记,找出自己所面临的“冷暴力”。随后,她又让自己回想他们在苏黎世度过的快乐时光。但后来她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幻想。他们既不曾共同生活,也不曾让彼此愉快。“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十分开心的。”彻底回想过去之后,她感受到一种“完全不一致的感觉,一些令人费解的内容,折磨且黑暗”。她忽然感到钻心的疼痛,感受到“无比真实的触感,仿佛置身黑与蓝的空间,疼痛撞击我的灵魂”。她深知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幸福,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只是一个美梦(他们的悲惨结局证实了这一点)。这种认知,当心灵以强烈的愿望,停泊在某处时,那同样令人难以忍受。总有一些令人费解和黑暗的内容与她相伴,与“冷暴力”相去甚远,而是一种严厉而冷漠的城市本身:“于我完全漠不关心。”但卢森堡以她的方式,选择接纳它自由地活跃在自己的心头,而非刻意抗拒。以这种力量,她才能够挑战不公平与非正义。她的伟大,正在于她从未尝试涂染黑暗,让心灵深处的捕食者显形,而是拥抱生活,仔细端详品味,去认知我们的历史中的一切。
我所呼吁的女权主义,正是这样一种矛盾的内容。它大胆而灼热地维护女性的权力,但从不借助错误而极端的身份认定和伦理传统来实现。它所要实现的是一种清晰、毫无争议的主张,从不用花言巧语来维护自己。我要说明的最后一件事,是性别本身,可以是慷慨的礼物,也可以是被消费的商品。女性主义者应当意识到的,是这种可能的变动意味着必然的改变,预示着性别的隐喻必然导致失败。此外的自我批判,则应当针对与世界的不可预知相矛盾的、政党式残忍与错误的许诺展开。这样一种女权主义,将接纳蹒跚与内在的受难,同时毫不犹豫地为它勾勒轮廓,为它提供正义层面的考量。这意味着我们要以巨大的体恤,来思索全部的性别。无论如何,所有出现在本书中的女性,都是卓越的女权主义者。但她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我呈现了如何构筑一个可行的未来,以及如何进入下一阶段抗争的画面。
楔子
第一部分巨星
1刀锋上的女人:罗莎·卢森堡
2以绘画对抗恐怖:夏洛特·萨洛蒙
3尊重:玛丽莲·梦露
第二部分底层
4荣誉”使然:莎菲莉亚·阿梅德,赫苏·尤尼斯和法蒂玛·萨西达
第三部分生者
5民主之形: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
6返乡之约:耶尔·芭塔娜
7损害之限:泰蕾莎·奥尔顿
后记
致谢
译后记
《独立报》:
这部作品为那些保持沉默的女性的思想和成就保有了一份颇有价值的记录。
《金融时报》:
在同时代的女权主义理论思考中,罗斯的论述显然是一次慎重而坚定的成功尝试。
《先驱报》:
令人敬畏的……想要忽视罗斯教授这些有关女权主义的发人深省的思考和严厉的批判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本兼具文学性与心理分析风格的佳作。它的问世是令人激动的,同时对于读者而言也将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挑战。
瑞秋.霍姆斯(《文学评论》):
在作为一名卓越的性别平等主义者的同时,杰奎琳.罗斯又是一位出色的叙述者……我们更需要倾听她既振奋人心,又不失冷静 关于“无所畏惧”的新型女权主义的呼喊。
妮娜.鲍尔(《弗里兹》):
在罗斯身上,人们仍可以看到这类宝贵却又稀有的思想特质:学术思考与社会现实的紧密结合。她书写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经历的黑暗且令人不安的真相,其目的并非是要将问题的讨论推向另一种极端,而是指向更加深刻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