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西马的迷狂
阿廖沙·卡拉马佐夫记下了司祭苦修僧佐西马长老的生平,这份根据长老自述所做的笔录在长篇小说中形成了完全独立的部分。这像是从一本古书中撕下的几页,又像训诫书①中的一个故事,自始至终是那么安详,自始至终充满了睿智。对小说的这一部分,我们考虑的已经不是分析,不是批评,而是仔细的阅读,以便捉摸到小说语言上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表现出的创作上的美妙之处。佐西马的生平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传略》,第二部分是《佐西马长老的谈话及训示》。我们现在来阅读故事的第一部分。佐西马不经意地回忆起他那已经故世的哥哥马克尔。“他比我大八岁,脾气暴躁,容易激动,但心地善良,从不嘲弄人,沉默得出奇,特别是在家里,不爱跟我、母亲和仆人说话。”这个年轻人看上去身体不太好,很瘦,很虚弱,“胸间常常作痛”,像是患了痨病。他尽管脾气暴躁,容易激动,却又“沉默得出奇”。描写这种出奇的沉默正是合乎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艺术特点:不是通常的沉默,而是某种特别的、别有深意的沉默。在他的心灵深处正在酝酿着某种感受,某种到了一定时候便会腾升在汹涌澎湃的年轻人情绪之上的感受。马克尔结识了一位流放到省城这里的学者,从后者那儿接受了宗教自由思想,这种宗教自由思想在生活中常常会变成无神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上帝,”他说。这些话把周围的人,特别是小小年纪的佐西马吓坏了。
当马克尔突然患病,得了急性肺痨时,脾气变得特别暴躁。他对什么事情都会生气;笃信宗教的母亲温柔地劝导他,他却火冒三丈,大骂毫无过失的“上帝的殿堂”。看来,他由于一生不顺遂而憋着一肚子怨气,现在要全部发泄在传统的圣物之上。可是,事情突然起了变化:他上教堂去祈祷,从那儿回来后变成了一个新人,怀着出乎大家意料的感情。“那年的复活节来得晚,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空气中飘逸着芬芳的气息……我牢牢地记住了他的模样:他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神态安详,面带微笑,虽然是个病人,可脸上的神情显得又活泼,又高兴。”对他来说,一切都笼罩在这种节日的喜悦中,闪耀着、散发着非人世的光彩。他曾经怒气冲冲地加以反对的东西,现在却渐渐进入他的心灵,同时又带来了另一种永恒的、神圣的东西。他开始从微小中看到宏大,从宏大中看到微小,由此在他的心灵中产生了感动。感动就是微小的个体在同宏大和永恒的接触中所出现的感受,由这种感受产生的情愫是悲喜交集的,或者换一种说法,它是含着眼泪的喜悦,是流露出喜悦的眼泪。当你目睹某件小东西,某种毫不起眼,微不足道,在人们日常琐事中弄得错综复杂,甚至好像被挤得畸形变态的生活现象时,便禁不住想赶快离开这个充满了渺小、委琐,令人厌烦的世界。但是你的心,你的那颗怀着最高生活真理的心却阻止你迈出魔鬼的傲慢的一步。心是看见了什么的,它看见了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它看见在广阔的生活海洋中,每一个个体同某个共同的本原进行着神秘的接触,而本原则通过这一个体把世界引向破灭,引向崇高使命的完成。只要捉摸到这种微小与宏大之间的联系,心灵中便会升腾起那种喜悦,那种迷狂,即称为“感动”的迷狂。这种感动充溢着病中的马克尔的心灵。“妈妈,你别哭,”他说,“生活就是天堂,我们大家都在天堂里,但我们不愿意知道这一点。假如愿意知道的话,那么明天全世界就会变成天堂了。”大家怀着温柔而又悲伤的心情听着他说话,就像平时人们听垂死的人说呓语那样。他的话尽管说得十分虔诚,但听起来像是病人的胡言乱语。有学问的医生认为马克尔精神有点失常。但是,后者那种在旁人看来像精神失常似的感动却蕴涵着伟大的真理。马克尔在自己的感动中看到了有时即便有着最敏锐的道德感的人也看不到的东西——自己对人们应负的责任,不仅仅是对人们,而且是对所有生物应负的责任。
“上帝的小鸟,快活的小鸟,”他在临终时说,“请你们也原谅我吧,因为我在你们面前也犯下了罪孽。,’世界上只洋溢着一种活生生的精神,这种精神的一切表现形式都神秘地,无意识地相互关联着,因而在实际上也是相互负有责任。马克尔倾心于这种新的思绪,对小鸟,对这些生性胆小的生灵产生了怜悯之情;大家都爱它们,可是它们是多么害怕人,害怕这个人间天堂的破坏者啊。在拥抱一切,领悟一切的欢乐的迷狂中,眼含着喜悦的泪水,佐西马的哥哥死了。
老人现在回忆起哥哥临终前的一件事,这件事在他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时近黄昏,天气晴好,太阳快要下山,斜晖脉脉照亮了房间。”马克尔双手抱住他的肩膀,充满深情地盯住他看了一会儿,说道:“好了,现在你去玩吧,代我好好地活下去!”夕阳拖着长长的斜晖,这即将消逝的白昼的最后一束亮光,这面临黑夜,面临夜的深渊——另一个上天真理的深渊出现之前的亮光此刻使佐西马年轻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生死是某种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大自然中存在着有关人类思想的所有象征物,如果倾听一下大自然的语言,观察一下由其创造的形象,即便不借助书本智慧也很容易捉摸到心灵所需要的一切,它们是多么美好,多么纯粹,人类的任何词语都形容不出来。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喜欢夕阳的斜晖。阿廖沙一生都牢记着童年时的一个情景,当时夕阳的余晖透过窗子投入到房间里,而他的母亲正同他一起在圣像前祈祷。佐西马也喜欢这种傍晚的阳光,我们将会看到,他在自传中是如何歌颂官的。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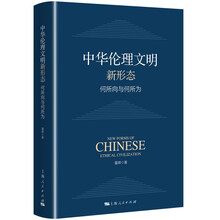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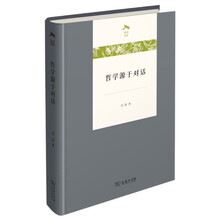








——索洛维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