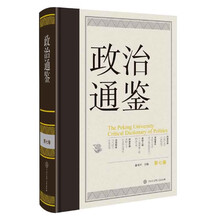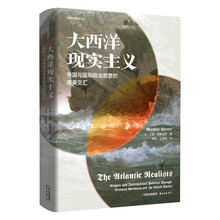显然,多元主义、整合、参与和动员都有特定的内涵,它们可以固定在,并且实际上保留在西方的探索与争论中。然而,在全球性的比较政治背景中,这些理念的特别性(specificity)被遗失了。多元主义失去了边界;整合也被毫无差别地运用于多元背景与非多元背景之中,参与和动员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重叠性的概念。多元主义没有了边界,是因为从来没人告诉我们什么是非多元主义。既然多元主义存在于某些地方,那么假定看来就是,多元主义将被发现“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任何地方。然而,不同程度的“什么”?原本打算恰当运用这种语言来表达准确性,事实却表达了令人困惑,不可捉摸——这实际上是对运用程度语言这种做法的讽刺。
就如我们知道的,特别性的损失起因于概念的延伸,而概念的延伸又反过来起源于沿抽象阶梯的不正确的攀爬:以牺牲准确性而不是以牺牲内涵(即减少一物之为该物的内在属性)为代价,试图笨拙地到达“概念移植的普适性”。
比如说,在对“多元主义”与“整合”的阐释与预言过程中所犯的可怕错误——而这一阐释与预言是通过对二者加以普适性的、非特别化的适用所体现出来的。如果我们说非洲社会不是多元社会而是部落社会,那么观点可能就是,部落式的分裂局面,不仅很难为整合过程的发生,而且很难为整合机构的发挥作用提供结构基础。实际上我的立场是,一个分裂社会的功能性需要或者反馈,与一个多元社会的功能性反馈或需要,是互相冲突的。比如,在欧洲,中世纪的分裂产生了君主专制。然而,如果多元主义化约成了一种空洞的一般性,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称非洲社会为多元社会,而且不幸的是,其带来的错误启发就很有可能是,我们就会预期非洲人会依照欧洲经验来处理自身的问题。
尽管多元主义、整合和参与起源于我们的民主经验——即起源于民主政体的环境中——但我们也要处理起源于极权背景的一套受限的术语。那就是源于军事术语的动员一词。该词尤其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的总体动员,特别是通过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经历而成为政治学词汇。不过,现在该词也运用于民主政体中。而且,我们常常抱怨说,我们的术语学是以民主为中心的,然而,我首先要抱怨的却是,我们未能利用一个事实,即我们确实拥有一些避免了民主偏见的术语。
踏足过非洲和东南亚的西方学者发现,我们的范畴并不适用,这丝毫不令人奇怪。据此,他们又认为,西方的范畴也应不适用于西方。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