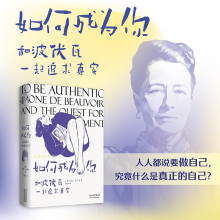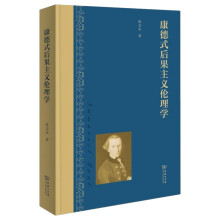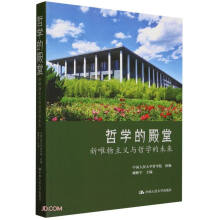在这里我要说明:首先可以使这个划界的权利在素朴自然的目光朝向中变得明晰可见,而且对于那些以心理主义方式拒绝我的“观念论”的人而言,它无论如何都必定还保留其价值。所以任何心理主义的经验论者也无法按照穆勒的方式对此做出任何改变:纯粹几何学与自然科学的教义相比是一个自身严格封闭的并且按照本质不同的方法来工作的教义之总体。他必须看到这里所做的区分,即使他事后会对此做出转释。反过来,即便没有几何学,一个心理主义者也可能会理解和赞同对这样一门相对于自然科学有其基本特性的学科之必然性的证明:只是他事后会以他的风格来对它进行展开解释。
“普全数理模式”在其所谓素朴的和技术的形态中,正如它在自然-客观的目光朝向中有可能被启动的那样,起先并不与认识论和现象学处在共同体中,与它相同的还有普通算术(它的部分领域)。但如果它在《导引》与第二卷的意义上也自身承担了现象学“启蒙”的问题,那么它就会随之而从现象学的源泉出发获得对那些在这里与在所有地方一样产生于存在与意识之相关性中的巨大谜团的解答;它随之也会获得那些惟有现象学才能做到的对概念与命题的最终的意义理解和保证:这样,它便从自然的逻辑学转变为本真的、哲学的和纯粹的逻辑学,而在此意义上,在哲学语境中所谈论的纯粹逻辑学恰恰就是哲学的学科。确切地看(并且与我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的较新阐述相一致),它不只是将认识现象学与自然-客观数理模式相联结,而是一种将前者(或者说,随它一起形成的纯粹认识论)运用在后者之上的做法。以类似的方式,例如通过引入那些从属于物理自然学说的认识论问题以及借助现象学对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物理的自然学说便从单纯的自然科学转变为自然哲学。‘而这适用于所有纯粹的和经验的学科。’
同时,人们现在也会理解我将我的哲学逻辑学之观念从那些与它平行的学科中分离出来的特定做法。如果将对象一般的形式观念(按照我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与质料对象区域相对置,那么和“分析的”或“形式的”本体论与含义论相对应的便是一系列质料的本体论或意义论,它们合乎那些因为引入可能对象性的“质料”而形成并曾被我称作“区域的”基本划界。如果人们也想将这种先天的区域科学称为“逻辑学”,那么,例如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便被扩展为一门普全的自然本体论一般,可以被称作自然的逻辑学。而后,与每一门这样的“素朴的”、须在“自然一科学”观点中建立起来的“逻辑学”相对应的是一门“哲学的”逻辑学,即一门在认识论和现象学上得到澄清的逻辑学。
对于在本书意义上的纯粹逻辑学——即最宽泛的和彻底理解的“分析学”——而言,为了现象学澄清的目的仅仅需要考虑某些最普遍的认识形态。而对于质料本体论来说,则尤其还要对相应的‘特殊’认识形态进行澄清性的本质思考;‘例如对于自然(physis)的本体论或逻辑学而言,要考虑的是自然构造意识的基本形式;对于心灵或精神的本体论而言,要考虑的是在构造上归属于它们的基本形式;如此类推至全体。’这样便消除了P.纳托尔普的一个建基于误解之上的、敏锐的指责(同上书),这个指责仍有一定依据,因为在我的著作的文本中缺少了一个具有刚刚给出的这种风格的阐释;但除此之外,对于这里所惟一关注的对“纯粹一逻辑学”领域进行哲学澄清的目的而言,这并不意味着一种真正的缺陷。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