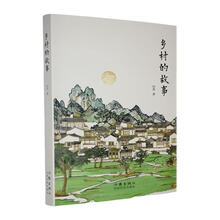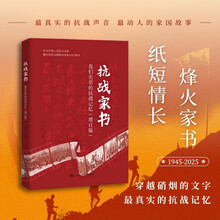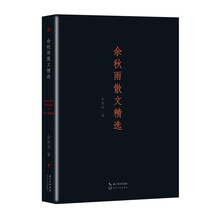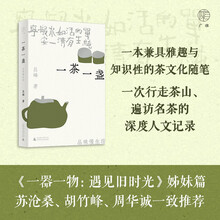故乡给我的感受总是这么庞杂,充满了苦难和泪水。无数次,我都试 图将故乡遗忘。可我越是这么做,越是忘不掉。我原以为,告别乡村,就 能告别过去,获得一种城市化的生活。但当真正来到城市后,我才发觉,自己作为农村人的特质是无法改变的。我的生活习惯,我的思维方式,我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是农民式的,与我置身的城市格格不入。我仿佛一 只蛙,离开了野地、草丛、池塘,闯入了别人的领地,只能沉默地活着。唯有故土,才能唤起我的自尊。稍有闲暇,我就朝乡下跑。走在熟悉的石板路上,内心的凄惶暂时得 以平复。苍翠的山峰首尾相连,白云在山顶漂移和游动,载着我的想象; 藤蔓爬满崖上的石壁,仿佛岁月的经纬;路边的树又沧桑了许多,经历过 时间的风霜雨雪,它们的年轮又刻下了诸多辉煌抑或暗淡的秘密。树权上 的几个鸟巢被风吹破了边沿,几根羽毛露在外面,那是生命留下的印记。曾经在里面安营扎寨的鸟儿,如今早已不知去向,说不定已经消亡。但它 们在这个巢里孕育的儿孙却依旧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替它们传宗接代。我常想,如果鸟也有乡愁,有一天,它们会不会带领自己的后代,飞 过千山万水,越过丛林沟壑,来瞻仰这个破旧的老巢,追宗问祖。且绕树 三匝,为遗失的故乡唱一首挽歌。我不能替鸟儿作出任何回答。或许,故乡原本就不只是为游子而存在 的。就像我,每次返乡都感觉故乡离我越来越遥远。它缥缈得如同一个梦 境,虚幻得好似一阵烟霞。当故乡在游子的心里逐渐变成一种伤怀和凭吊 时,它跟那个枯树枝上寂寞地空着的鸟巢,又有什么两样呢?回乡更多的是疼痛。我每次回去,耳朵听到的总是某某又不在了。这 些相继离世的人,大多是我的长辈。他们看着我出生,看着我长大。我穿 过黄四爷在寒冬腊月里偷偷地送我的一件旧棉袄,吃过春婶背着她男人给 我们的一碗白面粉;我至今还记得王大叔教我唱的人生第一首歌谣,更忘 不了李奶奶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帮我垫付的几块学费钱……这些平凡而普通,慈祥而憨厚的庄稼人,不仅养育了我,还教会我如何做人,以及活着的 尊严。从精神意义上讲,他们每个人都是我的父亲和母亲。可如今,他们 都已谢世。像春季过后的花朵,一朵接着一朵地凋零。走在故乡的山坡或 野地,无论是看到被荒草掩埋的旧冢,还是泥巴尚未干透的新坟,内心的 凄凉便如隆冬时节的寒气,从脚底蹿至脊背。我知道,在那些泥土下面,有我无法捡拾的乡村记忆,更有我未敢忘却的血脉亲情。少了一些人的存 在,故乡也就少了一种温暖。这递减的过程,使我每每提及“故乡”这个 词汇,都要鼓起绝对的勇气。我最近一次回乡,是我叔公的死。我们家族史上又一棵老树,在风摧 雨折中摇摇晃晃地坚守了六十九个春秋之后,终于断了。它断得是那样的 决绝和彻底,连根拔起,毫无留恋。这个性格倔强的老人,生前承载了太 多生理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折磨,孤独和恐惧时刻侵蚀着他,使他对人世 已经不再抱任何幻想。死对他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结局。我叔公一生乐善好施,本分老实,春种秋收,靠天吃饭。贫穷和饥饿 把他炼成了一个硬汉。他从不向人低头,凡事都往自己肩上扛。为把自己 的四个子女拉扯成人,他甘愿做牛做马,受尽人间屈辱。可当“荷子已成 莲叶老”时,他却落得个孤苦伶仃的下场。四个子女都不在他身边。两个 女儿远嫁他方。两个儿子,一个在重庆靠打工为生,另一个在近四十岁时 才靠入赘讨到一个寡妇为妻。一家人分别生活在不同的屋檐之下。即使在我叔公病重的时候,他的四个子女一个都没有回去看过他,给 他些情感上的安慰或精神上的支撑。他们都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斩断了血 缘这根藤。在农村,时常发生老人无人送终的事情。我们村头的赵婆婆,老伴比 她先走,子女又不在身边,单家独户住着。她长年有病,饮食起居全靠自 己拖着病体解决。因行动不便,平时门都关着。一天,有人路过赵婆婆家 门,喊话没人应。推门进去一看,才发现赵婆婆死在灶房背后,手上还拿 着把水瓢。尸体都臭了。苦难使亲情变得冷漠,冷漠又助长了悲剧的上演。因无钱去药店拿药,我叔婆只能隔三差五地上坡挖草药熬水给叔公喝。我叔公睡的床底下,塞满了大小的瓶瓶罐罐。那些瓶子里装满了水药。只要一踏进叔公的院子,一股怪味便扑鼻而来,带着死亡的气息。经过无 数次的努力之后,叔婆最终对叔公的病失去耐心,她早已厌烦了这个曾与 她同床共枕了几十年的男人。现在,她恨不得他快快死去,她已经心力交 瘁。当爱变成一种恨的时候,亲人之间就再没任何意义可言。我的叔公最终是带着痛苦走的。他躺在床上,神志恍惚,大小便失禁。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他临死前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再看自己的子女一 眼。他的子女们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上帝垂怜他,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把他召回了天堂。叔公的葬礼很是草率,连副像样的棺材都没有。叔公的四个子女匆匆 赶回来时,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么悲伤。他们只在叔公的灵堂前磕了几个头,烧了几沓纸,表情十分平静,仿佛灵堂里躺着的那个人,跟他们没有丝 毫的关系。叔公下葬的第三天,他们就各自启程,继续他们的生活去了。生和死,悲和欢,转瞬即成云烟。我站在叔公的坟前,不禁泪如雨下。这个让我百感交集的老人,再一 次把我这个故乡的叛逃者,重新拉回了故乡。或许正是因为疼痛,我才对故乡保持着敬畏。如今,坚守在故乡的人 一年比一年少。已经逃离故乡的人,如果没有一个充足的理由,是很难再 把他们召唤回去的。像我叔公的四个子女,他们根本不需要故乡。P2-5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