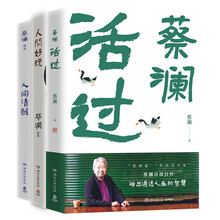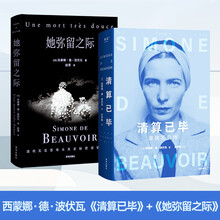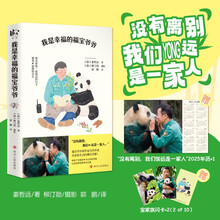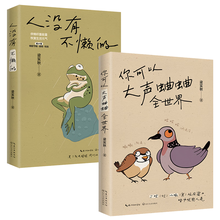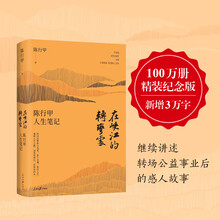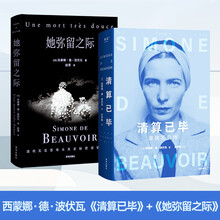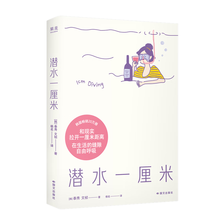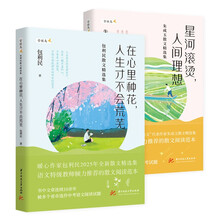《村上的事》记述了我们少年岁月那段历史时期(二十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方方面面的乡俗、村风。
樊秀峰在《村上的事》中,从生存的多角度观察生活和人生,寻找着人生策略,以他娓娓道来的笔触,勾画出了乡村四季变化、风土人情、沧桑变迁。自说自话的叙述杂识情怀,一方面表达坦然而又宿命的生存境界,反映了人和自然实质上的共时性存在,另一方面倾诉了长期的对于乡村的观察和体味,以及对每一个生意盎然的生命个体的理解、尊重和感叹。秀峰在行文时省却了奇异的故事和华美的辞藻,以一种散淡保持了一份悲悯与谦逊的情怀。
乡村是一片光而不耀的风景,是一缕深切绵长的记忆,是一腔亲切真挚的情怀。
回望渐行渐远的乡村岁月,我也在不断地反刍着人生,心中总会不由自主地涌起一些温暖、庄严的滋味;有时,也会感到有些微微地发疼。我想,这或许是因为一种寻找,一种缅怀,或者是一种惦念和眷恋吧。
岁月的流逝是缓慢的,那些乡村往事并没有走远——远的,只不过飘落在故乡的村头;近的呢,其实就扎根在自己的心头。
我是从村子里出发的,二十多年后,又借手中的笔不断地返回到那里。我写《村上的事》其实就是想用手中的笔,描绘出自己心中的“故乡的原风景”。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