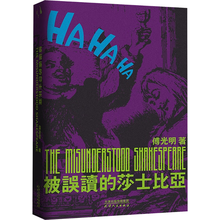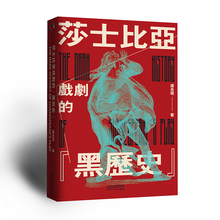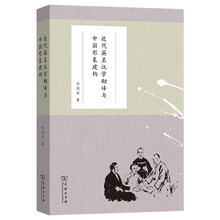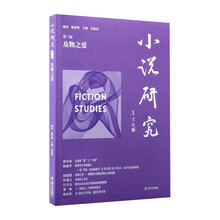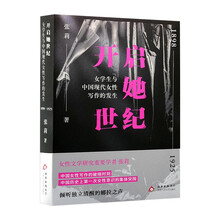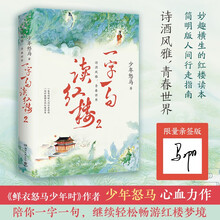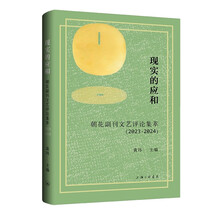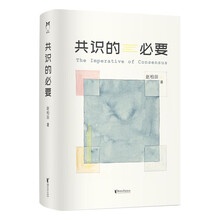周公对于礼乐文化的这种改造,使原本事神致福的礼乐,变成“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的治国利器,正如《礼记.曲礼》所言:“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乐由庄严肃穆的宗教庙堂走向了贵族的日常生活,由敬神娱神的礼器乐舞变成了人间秩序的规范,不但涵盖了道德、习俗、法律、政治、人伦、教育、军事、宗教、外交,而且与周人的日常生活也密切相关,诸如祈子、命名、冠笄、嫁聚、丧葬、相见、朝聘、宴飨、射御、籍田、会盟等活动,无一不有与之相应的礼典。“周人尊礼尚施”(《礼记.表记》),礼乐也因此成为周代文化的特定称谓。<br> 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代统治集团,对原始礼乐的这种文化改造,使它从原始宗教中摆脱出来,从天人之际走向人人之际,为礼乐文化的发展,注入了人文主义的因素。<br> 在这种人文精神的统摄之下,经过周公制礼作乐,西周的礼乐文化灿然大备,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形态。<br> 1.名目众多,繁文缛节。<br> 周礼的名目极为繁多。《礼记.礼器》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虽有些夸大之辞,但还是比较客观地折射出周礼名目繁多的特点。对周礼分类,“三礼”中有五礼、六礼、八礼、九礼之说。①邹昌林在《中国礼文化》一书中例举周人礼仪近百种,并将其归纳为7类。其中属人生礼仪的有祈子礼、胎教之礼、出生礼、命名礼、保傅礼、冠礼、笄礼、公冠礼、昏礼、仲春会男女礼、养老礼、丧礼、奔丧礼、祭礼、教世子礼、妇礼等16种;属生产礼仪的有籍礼、射礼、蚕桑礼、养兽礼、渔礼、蒐礼、田猎之礼、献嘉种礼、御礼、货力、饮食之礼等11种。<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