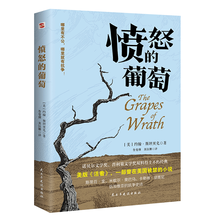舍拉德镇的葬礼<br> 四个嬷嬷头戴修女帽身穿蓝色长袍手戴绢丝手套,分成两列,走在队伍的最后。其中两个举着的阳伞仿佛上个世纪的古董。她们前面,沿着从舍拉德镇教堂通向公墓的山路上,三百多人走在一辆由两对萨莱尔母牛拉着的干草车后面,牛角的形状仿佛敞开的竖琴。以前,田里割草开沟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干草车,以及扬起木搂耙挥汗如雨的农夫农妇。干草车上放着一具狭长的棺木,盖着圣灵骑士的白底红十字旗帜,十分耀眼。两个红衣主教紧随棺木。他们的出现有些出人意料,可是葬礼上的哪个环节不出人意料?主教长袍上身裁剪合度,从腰线开始像花冠一样散开垂到地面上,简直像从费里尼影片中宗教服饰表演里走出来的人物。其他人跟在主教身后。<br> “所有人都来了。”<br> “嗯,差不多吧。”<br> “那些还活着的人。”<br> “那些没有拒绝公主邀请的人。”<br> 让-沃尔金斯基纠正道:“那些公主愿意邀请的人都来了。”<br> 人群中发出一阵过于欢快的笑声,显得有些牵强。让·沃尔金斯基九十一岁,是马特乌斯的哥哥。谁都不认为这两兄弟关系和睦,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毫无疑问,马特乌斯是二十一世纪初在世的最伟大的画家,尽管画家本人听到这个称呼时总是露出一丝善意的嘲讽的微笑。<br> 两兄弟中,只有让·沃尔金斯基继承了父亲的姓氏,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br> “他们俩长得真不像……”文化部长低声嘀咕。他紧随主教和亲属,走在第一排。沃尔金斯基像个侏儒,而画家却是个巨人!<br> 乔治·比尔巴两个月前刚刚被任命为文化部长。糟糕的是他从来没有读过沃尔金斯基的作品,甚至不知道画家的哥哥原来也画画。也许他现在还继续画油画,甚至素描。律师雷奥乃诺·巴杰利走在文化部长身旁,他是意大利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律师身后跟着他的家人。<br> 首先是他的妻子阿德里娅娜,不少作家觉得有义务将自己的一部作品题献给她,感谢她在阿玛尔菲海岸或科莫湖畔热情的款待。随后是律师的妹妹朱莉娅娜,她在九十年代初昙花一现的右派政府中担任过国务秘书。朱莉娅娜身后的男人肤色黝黑,长得酷似死去的画家。他叫杰尼·波基,马特乌斯的老朋友,走在他左右两旁的是他的两个孙女,都有着典型的托斯卡纳人鲜明的轮廓。再往后是各大艺术场馆的负责人,在队伍里窃窃私语。巴尔尼耶是蓬皮杜中心的主席,他说马特乌斯喜欢两个女孩中更年轻的那个,还帮她画过一幅肖像。伦敦泰德现代艺术画廊的负责人耸了耸肩,不置可否。二十年来,他编纂的重要绘画作品目录中,没漏过一幅马特乌斯的作品。托马斯·瓦德一强森几乎和马特乌斯一样高一样瘦。他拄着拐杖,吃力地走在岗达尔地区舍拉德镇山谷的小路上。他身旁是米歇尔·凯斯纳,一位一直为画家歌功颂德的美国评论家,也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坑坑洼洼的石子路上。山路顺着峡谷延伸,一直通向二十多公里外一个巨大的古冰川,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马特乌斯总是拒绝画这片风景。尽头的玛丽峰高耸入云,狭窄的山脊急速下降,形成七道星形的峡谷,仿佛微缩的塞尔文山景。在奥弗涅省这片静谧的风景中,马蒂亚斯·沃尔金斯基成为永恒的马特乌斯,又永远地安息在这里。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画家去世了。人们从欧洲各地,从美国、中国和日本赶来参加他的葬礼。<br> 几个星期后,克洛德·巴尔尼耶发表了一篇简短但充满感情的文章,当然,也没忘记对当天舍拉德镇葬礼的仪式冷嘲热讽一番。文章就叫“马特乌斯的葬礼”,他从绘画的角度回顾了马特乌斯的葬礼,提到了画家公开表示反感的埃尔·格雷科,还有他毕生热爱的库尔贝——马特乌斯正是在奥尔南山区举办了最后一次画展。巴尔尼耶描绘了由配着黑色鞍辔的奶牛拉着的灵车,还有一匹白马,五十岁那年,马特乌斯一时兴起,骑了一匹高头大马从当地人称的面包顶一直漫步到圣洗谷,于是有人从农场牵来一匹又高又驽的耕地的马表示纪念。巴尔尼耶还提到,队伍中穿着骑马长裙侧坐在马背上的马术女演员长得酷似马特乌斯油画《桑德拉的肖像》中的人物,创作这幅作品时,马特乌斯是瓦兹侬家族在美国广场旁的沙龙里的座上宾。巴尔尼耶并没有追寻这个女孩的身份,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没有见过她。<br> 巴尔尼耶准确地表达了来宾当天的感受:乡下的葬礼变成一场时装表演,照片登上各种今天我们所谓的名人杂志——尽管马特乌斯的中国妻子只授权他们的摄影家朋友居尔蒂斯·布勒南独家拍照。死者早就料到葬礼的盛大规模,对仪式的每个细节都做出详细的规定。葬礼成为他一生的缩影:前来出席的,有曾经在自己家中款待过画家的意大利和英国友人,有画家在阿尼夫镇和萨尔茨堡的朋友,有他的画商以及来自纽约和全世界的收藏家,还有为求墨宝不惜重金的日本崇拜者——画家和他们的关系最为微妙。这些来自日本的崇拜者和全世界的收藏家都对画家最后的作品翘首以待,而画家本人却对此讳莫如深。两年来,画家把自己关在阿尼夫镇花园尽头的画室里,同时创作三幅油画,禁止任何人参观。当然,葬礼上还有少数几个尚在人世的画家的作家朋友,记者,评论家,部长——老好人比尔巴并不是唯一的一个部长,附庸风雅的人,和那些四十年前的社会名流。所有的文化官员都来了,走在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画家的灵柩之后。人群中有许多人曾经上过头版头条:眼前的这个演员曾经写过小说,当过另一位老画家的情人,现在已经被媒体遗忘;还有这位面容古典、风韵犹存的女明星;还有其他的明星,他们的面容在这个世纪初显得如此苍老。走在队伍的最后的村民交头接耳,讨论这一位是否就是他们经常在电视里看见的明星让一雅克·N或者玛丽·B。在这列幽灵般的队伍里,几个年轻的女孩子显得格外醒目。巴尔尼耶称她们为“妙龄少女”,这些漂亮的妙龄少女穿着时尚的克里斯蒂安·拉夸或香奈儿时装,显得“格外地荒唐可笑”。荒唐可笑,巴尔尼耶用的就是这个词。不过,他错了。她们的出现并不荒唐,一点儿也不。真正了解马特乌斯的人,像他的律师昂普拉尔、杰尼·波基、巴杰利、让·沃尔金斯基都心中有数,不但没有流露出讶异的神色,反倒对大师最后的闲情逸致露出一抹微笑。<br> 最后,让一勒内·勒克莱尔致辞。他提到皮耶罗·德拉·弗朗杰斯卡、普桑、库尔贝,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可是当他提到让一乔治·雅丰的名字的时候,在场的知情人都开始面面相觑。雅丰和马特乌斯曾经是好朋友,后来不知为什么闹翻了。十年前雅丰去世的时候,马特乌斯曾恶言相加,说这位伟大的基督教诗人更像耶稣会会士,或者冒牌的多明我会修士。“他们有同样的热情,它在画家的笔下变成浓烈的色彩,在诗人笔下成为炽热的诗句……”发言的时候,勒克莱尔的眼光扫过在场的部长和文化官员,停在一位全身黑衣手持一朵白玫瑰的老太太身上。人们并没有立刻认出她就是诗人的遗孀贝娜黛特·雅丰。谁都没想到她会受邀参加画家的葬礼。勒克莱尔随即开始描绘马特乌斯的作品《阿浦松的田园》,大多数崇拜者对这幅油画的每一个细节都了然于胸:一线阳光照亮作品的中部,三道岗达尔地区隔离夏季牧场的灰色石头墙仿佛伸入云际。当勒克莱尔说到作品主体略显沉重的格罗蒙峰从背景中脱颖而出时,他突然停下来,对围成一圈站在马特乌斯灵柩周围的送葬队伍大喊:“快看!小树林的上方!”<br> 他的手指向格罗蒙峰。一缕金色的田园的阳光照在小树林上方的山脊上,马特乌斯的朋友们不自觉地走入了他的作品。<br> 谈论死去的画家<br> 讲述马特乌斯。讲述他的绘画,当然。他的绘画,还有他的一生。为马特乌斯写传记。他的一生。他的一生?我已经听见他的朋友们的嘲笑声,他真真假假的朋友们。写马特乌斯的传记?你开玩笑!八十多年来,他都拒绝谈论自己!我仍然能听见他的声音,他习惯在阿尼夫镇的小办公室里关上门“谈话”。对他而言,“谈话”可不是坐在桌子旁闲谈或边喝酒边聊天这么简单的事情。访问者借难得的机会向他提问,而画家本人却总显得心不在焉。唉,马特乌斯从来就没有宣泄的需要,他总是面带微笑,若即若离。尽管如此,我第一次去白木屋拜访他的时候,还是向他提了个问题。<br> “您的青年时代呢?人们都不知道您是如何度过青年时代的,只知道您童年曾……”<br> 马特乌斯笑着打断我的问题。<br> “又来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