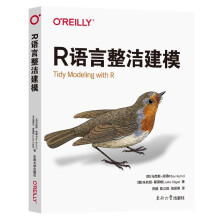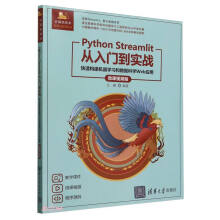跨国的女性主义实践取决于跨过地点、身份,阶级、工作、信仰等方面的分歧,建立起女性主义的团结一致。在这样支离破碎的时代,建立这样的联盟是非常困难的,但却是非做不可的。全球资本主义摧毁了这样的可能性,但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这是漂泊不定的知识分子取代根深蒂固的知识分子、后现代主义话语铲除“原生知识分子”的时代。在浩瀚无涯的地平线上做全方位的航行,有关移位的语义就会过多;我们总是“某人的他者”,总是想避开对同化的嘲弄。真正的选择——是社团还是种族,是种族的脆弱性还是新宗教教旨主义——那些因民族烦恼演变成悲剧的选择,在流亡者的想象中依然模糊不清。
立法和政治意义上的表现(少数人“代表”一大群人)现在被当作一个应该质疑的特权摆到了突出的位置。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背景下,这就是说某些代表,甚至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已经在代表别人(指美学意义的创造符号、编故事、画图画以及为此构建理论,等等)。正是这种未经授权就获得的代表权(发言权)使那些对非西方人的歪曲和种族主义的描述得以在客观再现(重造现实)的名义下出笼。因此,即使表面上中立的美学表现也是带有动机的政治表现击拈制行为。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