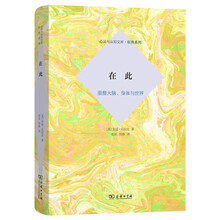蒋庆先生之思想史意义——《政治儒学评论集》代序
去年,笔者曾在微博上多次说过这样一句话:“蒋庆先生是六十年来大陆唯一思想家。”此论断在网络上固然引起巨大争议、甚至是嘲讽,网下以政治思想为专业的学者朋友,也多有微词。
然我不为所动,始终坚持这个看法。任重先生编辑这本《政治儒学评论集》,邀我为之作序,得机会参考诸位先进之赞与弹,并因此而系统地重读蒋庆先生三本大著:1995年出版之《公羊学引论》、2003年出版之《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2012年出版之《再论政治儒学》,对自己的看法,比这更有信心。
为论证这一观点,我撰写了这篇也许有点太长的序言。我将指出,蒋庆先生在四个方向上打破了百年来中国思想界营造的并被人们普遍信持的思想、价值和观念迷信,树立了中国思想之主体性,建立了中国人思考政治问题之基本范式,因而足当唯一思想家之誉。
一、恢复儒学之完整性:政治儒学乏提出
讨论蒋庆先生之思想贡献,首当注意者自然为“政治儒学”概念之标举。
政治儒学乃针对心性儒学而提出。在“科学与玄学大论战”中,张君劢先生疾呼“新宋学之复活”,在当时全盘反传统的特定语境下,具有重大思想史意义。
20世纪初,炫目于西方之坚船利炮和社会治理,儒家士大夫群体发愤学习模仿,乃有废书院、废科举、废读经之举。此前,经、史、子、集的中国固有思想学术体系与以经学为主的教育体系互为表里;教育体系之全面西化,导致中国既有思想学术体系逐渐崩溃。在新式学校接受教育的学者、知识分子则秉持历史主义理念进一步断定,中国既有思想学术体系是过去的、古代的,不具有回应现代问题的能力。曾被视为常道的“经”被历史化,成为人们运用现代价值、知识进行研究、剖析,最后予以清理的对象。
也正是依据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态度,西方汉学家曾提出一个著名命题:儒家已“博物馆化”。确实,自新文化运动之后,在主流思想学术界,儒家已经完全变成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主题,此即胡适等人提出“整理国故”之预设,中国既有之思想,主要是儒家,已成为“故”了。
在这种背景下,具有保守主义倾向之学人如梁启超、张君劢、熊十力,一心护持中国文明,然欲进而不能,乃不能不有所舍弃,沿着张之洞“中体西用”之思路,退守“心性儒学”,集中于探究个体成德成圣之学,而将公共领域交给西学,也即科学与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虽然是作为新文化运动之反动登场的,仍带有该运动之深刻思想与观念铭印。
此后,新儒家基本上就是心性儒学,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贤于1958年发表之《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断言:“此心性之学,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作为现代中国最为有影响力的思想流派,新儒家的儒学观塑造了学界、公众的儒学观,人们普遍以为,儒学就是、也应当是心性之学。这种儒学观影响极大,港台海外儒学基本上是心性儒学;大陆儒学于20世纪90年代复兴之后,也几乎皆为心性儒学及其衍生物和心性儒学史之研究。
毫无疑问,心性儒学在20世纪艰难的思想、知识与政治环境中,守护了儒家之命;心性儒学之思想成就,比如牟宗三先生所构建之宏大哲学体系,也是20世纪中国唯一可观的思想与哲学成就。不过,心性之学确实遮蔽了“儒家的整体规划”,它的成立也确实以拱手让出公共生活之治理于西方思想和制度为前提。由此导致港台新儒家身处大变动的时代,却无力参与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制度之理论构想,更无力参与制度构建之实践过程。因而,在台湾地区转型之后,新儒家迅速陷入困境,而在社会中不具有强大的发言权。而台湾地区社会虽为一儒家社会,却缺乏足够的思想与观念自觉,没有强有力的儒家声音提撕、引领社会。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