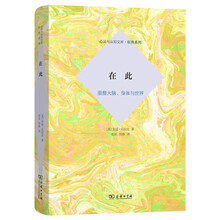一孤独者的身影
1.1
司马迁怀着崇敬之情,以悲剧性的笔调,在《史记》中为孔子作了传,叫“孔子世家”。
孔子是春秋末期鲁国人,名丘,字仲尼,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孔子的先祖是宋国贵族,殷商王室的后裔,后因避祸而逃至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个武士,六十多岁“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可谓清贫,对此,他记忆深刻,后来对弟子们回忆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成年后的孔子身材魁伟,气象不凡,身高“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
孔子自幼好学,尤其热衷于对礼俗的钻研,因为博学,年轻的时候就远近有名了。孔子十七岁的时候,鲁国大夫孟孙氏病危,谆谆告诫自己的儿子:“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因为学问好,大概三十岁时,孔子开始授徒讲学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办私学的人,他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孔子一生杏坛挥鞭,“弟子三千,贤徒七十二人”。
不过,孔子最大的人生愿望还是去从政,他不仅怀抱崇高的政治理想,而且具有将理想付诸实践的政治才干,他拒绝空想。不过,从政愿望的实现并非易事,直到五十一岁时,他才步入鲁国政界,先是担任中都宰,政绩不错,后为司空,很快又升为鲁国大司寇,算是高官要职了。
孔子从政,为的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挽救“礼崩乐坏”的混乱时局。然而,孔子并没有能够在鲁国成功地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五十五岁的时候,孔子带着弟子们,离开了鲁国,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成了名副其实的“流浪的君子”。颠沛流离,一路下来,就理想的实践而言,一无所成。
孔子结束流浪的生活状态而重返故国时,已经六十八岁了,垂垂老矣!他不再考虑从政的问题了。在人生的最后五年,他专心致志于典籍的整理和编修,鲁国人尊称他为“国老”。
1.2
司马迁的孔子传勾画了中华文明史上一个伟大的孤独者形象。
孔子去世的时候,鲁国国君鲁哀公还年轻,二十来岁,他亲自为孔子写了祭文:“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鲁哀公呼天抢地,怨恨上天为何不愿大发慈悲,让国老长寿更长寿,以护佑他稳居君位;孔子的去世,使得自己孤苦伶仃,承受孤寂无助的煎熬。鲁哀公深情地哭诉:尼父啊,失去了你,我怎消心中的忧愁!
鲁哀公是国君,孔子是他的臣子,国君称臣子为“尼父”,可见他是何等地尊敬孔子!
问题在于,鲁哀公何以要在祭文中表达自己内心世界那种巨大的孤独和寂寞的感受?他或许相信,只有孔子能够体会他内心的孤独和寂寞。因为孔子本人,尽管杏坛挥鞭,“弟子三千”,桃李满天下;即便在年过半百之后,无可奈何地离开故国,周游列国,一路上也还是受到好多国君、大夫们的礼遇和尊重,但他仍然难以排解自己内心世界的孤独感。
孤独者的知音必定也是孤独者。司马迁能够领会鲁哀公倾泻的孤寂情绪,更能深切地体察孔子内心世界孤独感的精神意蕴和力量,因为他也是孤独者。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事件辩白真相,而激怒了汉武大帝,而下狱且遭宫刑之辱,仍在痛苦而悲凉的心境中忍辱著书;在《报任安书》中,他以无坚不摧的气魄,向朋友倾诉了支撑自己著史的伟大力量源泉:“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说,孔子周游列国,在途径郑国的时候,“与弟子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坦然承认自己的无家可归,就像丧家之狗一样。这是内心世界强烈孤独感的表达。
就在孔子去世前,弟子子贡去看望他,师徒一见面,孔子泪流满面,悲叹而歌:“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然后,他对子贡说:“天下无道久已,莫能宗予。”孔子最后一次思量这个世界,他相当的绝望,不报什么希望了!
可以肯定地说,在内心世界,孔子比鲁哀公更为孤独!
1.3
国君和臣子都陷入了难以化解的内心世界的孤独,这一定是一个混乱的时代。
中国古代历史上所谓的“先秦”,指的是大秦帝国建立之前的夏、商、周三个王朝。周朝包括“西周”和“东周”两个阶段;“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最通行的意见是,“春秋”时期开始于公元前770年,结束于公元前477年。也就是说,孔子是春秋末期的人。孔子于公元前479年去世,他去世两年后,中国历史就进入战国时期了。战国时期结束于公元前221年,这一年秦王嬴政统一了中国,开创了大秦帝国。
顾名思义,“战国”时期是一个战争的时代,是一个刀光剑影的时代,是一个血雨腥风的时代,是一个混乱不堪、民不聊生的时代。战争是残酷的。可战国时期不是突然来临的,战争的祸根就埋藏在春秋时期。
史家对于春秋时期的总体判断是“礼崩乐坏”。夏商周三代,尤其是通过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而建构的礼乐文明秩序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才最终酿成旷日持久的战争灾难。
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权威丧失,窝窝囊囊;各诸侯国彼此征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大夫专权,君位难保;家臣乱政,士子流离失所;黎民百姓就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孔子批评那个时代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一切都乱了,没了章法。
所以,孔子说:“天下无道久矣!”
司马迁傲立历史之巅,深切洞明孤独者孔子的崇高精神意义,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坦言:“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脩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这意思是说,孔子生逢乱世,其思想道路的选择、政治理想的追求、精神信念的坚守注定了孤独者的悲剧性气质、性格和命运。
1.4
鲁国本是西周初年“制礼作乐”的周公的儿子伯禽的封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可到了春秋时期,鲁国长期以来是“三家”大夫专权,国君早已是苟且度日。孔子升任鲁国大司寇后,试图消弱大夫的权势,还政于鲁君,但无力回天,以失败而告终,被迫“周游列国”。
因而,鲁哀公在给孔子的祭文中表达自己内心的孤独和寂寞,不是作秀,他知道孔子地下有知,是一定能够理解他的内心世界的。
鲁哀公能够理解孔子吗?这无论如何都是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鲁哀公之所以敬称孔子为“尼父”,是因为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孔子超凡的智慧和伟大的人格力量,孔子能够带给他心灵世界以温暖和慰藉,尽管他很可能对孔子深邃的思想世界无可名状,说不清、道不明。
其实,何止鲁哀公如此,那个时代的人们又何尝不是如此!
《论语?子罕》中记载,颜回面对老师博大而深邃的思想世界,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论语?子张》中还记载,叔孙武叔在公开场合夸赞子贡比他的老师孔子还要贤明。子服景伯把这个意见转告给子贡。子贡听说后,打了个比方以郑重回应:“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子贡知道,能够理解孔子的人实在太少了,连知道走进孔子思想世界路径的人都微乎其微,那些不得其门而入的人如何可能正确评价孔子!
颜回、子贡是孔子的高足,他们崇敬孔子;而且,他们深知,孔子的孤独绝非常人的孤独!他的孤独是先知的孤独,是圣人的孤独,是亘古未有的旷世孤独,也因此是圣洁而伟大的孤独。
当然,孔子在世的时候,还是从弟子们那里感受到了温暖与慰藉,弟子们视先生为先知和圣人,在心灵深处敬仰先生,尽管孔子自己从不敢以先知和圣人自居,《论语?述而》中记载了他的话:“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弟子公西华感叹地说道:“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弟子们达不到先生的高度和境界,但深知捍卫先生尊严的意义。当时,挖空心思诋毁孔子的人不少,《论语?子张》中就记载,那位夸赞子贡的叔孙武叔公开诋毁孔子,子贡愤怒了,简直就是作“河东狮子吼”:“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孔子去世后,弟子们为他守孝三年。
子贡把家搬到孔子坟墓旁边,为先生守墓长达六年。
司马迁在其孔子传的结尾写道:“《诗》有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1.5
孔子的孤独和绝望渗透着一股强大而神奇的力量,侵润着人们的心田,感召着人们的心灵,启迪着人们的思想。孔子去世后,他创立的儒家学派继续壮大,儒生们对先师思想世界的理解、阐释和争论从未停止过。
《韩非子?显学》中有言:“自孔子死后,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就是“孔子而后,儒分为八”的著名论断,其实,先秦儒家内部派别林立,远不止这八派。
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派也因此逐步渗透、融合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孔子不再是一个孤独者,“吾道不孤”;孟子称赞先师为“圣之时者”,认为孔子是一个能与时俱进而通权达变的圣人,绝不是一个泥古不化的迂夫子。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六国而开创帝国政治世界秩序的同时,孔子传承并开新的心灵世界秩序也在越来越强劲地生长起来;而且,两个世界最终必定走向统一。因为,没有灵魂的政治是短命的。
孔子去世后300多年,汉武大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希望能够通过弘扬孔子儒家的思想而凝聚起大汉民族的精神之魂。
汉武帝之后,历朝历代尊孔祭孔,加封孔子,孔子获得了很多谥号,比如唐玄宗给孔子的谥号是“文宣王”,元武宗给孔子的谥号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到了明嘉靖九年,明世宗最后确定孔子的谥号为“至圣先师”。
孔子在生命垂危之际悲叹道:“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他或许没有想到,自己去世后能够被中华民族尊奉为“万世师表”。“万世师表”是清康熙皇帝为孔庙大成殿的题词,是对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孔子敬仰和称颂的总结。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哲学中,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说。他指出,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几个世纪里,在中国、印度和希腊等几大主要文明区域里,几乎同时出现了自己的文化“先知”,他们在相互隔绝、彼此没有信息交流的背景下,差不多同时完成了一次意义深远的精神转变:“那是些完成了飞跃的民族,这种飞跃是他们自己过去的直接继续。对他们来说,这一次飞跃如同是第二次诞生。通过它,他们奠定了人类精神存在的基础,以及所谓的真正的人类历史。”
孔子作为“轴心时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先知和圣人,他直面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明确地把生命的尊严和人性的升华作为头等重大的思想主题加以深思;他追问重建政治、社会、人生秩序的“大道”;他坚信人不仅仅是动物式的活着,还要思索活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活的质量问题、活的信念问题。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因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而不断地得以延续和提升。孔子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精神导师,他求“道”、体“道”、言“道”、传“道”、证“道”、护“道”,终其一生,锲而不舍,他宣称“朝闻道,夕死可矣”。
当代学人韦政通先生说:“相对于神之子,孔子可以说是大地之子,这不只是因为他关怀的是今生今世的人格、文化、社会、政治等问题,而是由于他的生命、他的精神,彻彻底底是植根于大地之上的。”
在中华文明史上,孔子有两种基本形象:一是教师形象,二是立法者形象。“至圣先师”的谥号是对这两种形象合二为一的表达:一是内在心灵秩序的立法者,一是外在生活秩序的立法者,都是“立法者”。
这个意义上的立法者无疑是大学问家,是大思想家,是大哲人。孔子正是以孤独者的生存勇气、担道者的高蹈情怀和哲人的慧心睿智,实现了中华文明在“轴心时代”的“精神突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