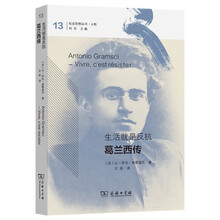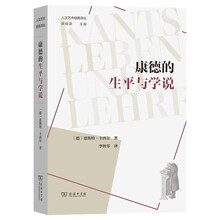第二节 孔子出生·少年立志
人的一生,是由不同的成长阶段组成。不过,客观地讲,人生的每个成长阶段,对人之一生的影响,作用轻重却是不同的。寻常人也罢,伟人也好,幼年、童年和少年时的成长经历,相对来讲是最重要的人生阶段。孟子讲到杰出人物的成长历程时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意思是说,如果上天打算让一个人承当重大使命,就会从精神、身体和行为等方面对这个人进行最严苛的考验,目的就是培养他坚强的品格,让他的身心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孟子这个著名的“大任”说,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是针对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而发的,不过,对于孔子来说,这种考验从他出生之后就开始了。虽然不能说早年的生活磨难一定可以造就伟才,但它有助于伟才之成长却是毫无疑问的。说到孔子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虽然种种相关史料之所述多有抵牾,但总的来讲,生活在其中的孔子是相当不幸的。
出生,童年的磨难
根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叔梁纥与颜氏女的婚配是“野合”的结果。因为在这篇传记中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所谓“野合”的确切意思也就一直存在着不少的争议。
事实上,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从来就不乏有人望文生义地理解“野合”的意义。有人误认为是叔梁纥强抢民女,更有甚者,认为孔子乃是私生子。其实,在孔子时代,“野”的本义是指城市和近郊之外的田野之地,就是距离城市生活和城市文明较远的地方。因为生活在这种地方的主要是农夫,身处社会下层,没有机会接受礼义教化,所以,以这部分人为代表的相对质朴、不加修饰的言行,也称为“野”,这是“野”字的最直接的引申之义。孔子批评弟子子路说:“野哉,由也!”使用的就是“野”字的这一引申之意。
很明显,“野合”的本义与“野”字的上述引申意义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孔子本人就使用过“野合”之辞。《左传·定公十年》对孔子相礼“夹谷之会”的记载中,当齐景公要求在盟会之后另外招待鲁定公时,孔子意识到齐国人不怀好意,是想另找机会为难鲁君,于是就提出了反对意见。孔子认为:“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就是说,在朝廷之外的地方不适宜举行正式的宴乐,因为正规的礼器不能携带出朝廷。另外,《春秋·庄公二十三年》记载说:“萧叔朝公。”意思是说,鲁国的附庸之国萧国的君主来朝见鲁庄公。因为这时候鲁庄公并不在鲁国都城,而是在另一个地方会见齐国君主,所以,杜预就解释说:“凡在外朝,则礼不得具,嘉礼不野合。”显然是间接引用了孔子的观点,意思是说,因为在都城之外,没有条件举行正式的会见仪式,鲁庄公就没有举行正规的仪式会见萧国君主。这就说明,在“周礼”的规定中,正式的礼仪不能“野合”,即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环境下简陋举行。这里的“野”就是不合正式规矩的意思,“合”则是举行或完成的意思。
所以,《史记·孔子世家》所说的叔梁纥与颜氏女的“野合”,是说二人并没有举行正式的婚娶仪式。在儒家的传统经典中,有一部专讲士人之礼的《仪礼》,大约成书于战国到秦汉之间。在这部书中,专有一章《士昏(婚)礼》,详细记载了“周礼”对士人婚娶的标准要求,那种繁杂程度是今人所无法想像的。尽管《仪礼》之内容添加有作者理想的成分,尽管在孔子时代“周礼”的约束力正在下降,但在《孔子家语?本姓解》的记载中,当叔梁纥与颜家的亲事定下之后,“徵在既往”,所谓婚娶仪式,也不过只有“庙见”一项。如果这也叫婚礼的话,即使在后代,即使在今天,这个婚礼也过分简单甚至简陋了。一言以蔽之,颜徵在只是被迎娶到家庙,而并没有在城中举行正式的迎娶之礼,就开始了家庭生活。
那么,造成“野合”的原因是什么呢?传统的解释都把重点放在二人在年龄上的悬殊差别。或者说二人年龄差距太大,不符合当时的礼仪规定;或者说叔梁纥年龄已经超过了正常的生育期限,属于非正常结合和生育。这样的意见有一定道理,但却并不周全。因为《史记·孔子世家》和《孔子家语》都没有说明叔梁纥迎娶颜徵在时的具体年龄,即使当时有相关的礼仪或习俗的规定,也无法确知叔梁纥是否违反了这样的规定。
其实,考虑到《史记·孔子世家》对于孔子一生的记载虽然相对来讲是最详尽的,但却也是最繁乱的,并且对于“野合”二字也没有相关的解释和说明,因此,不去细究“野合”之含义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的。然而,又考虑到“野合”之说的巨大影响,任何讲述孔子出生的文本,都必须提供一个明确的意见。既然各种记载都缺乏确切记载,所以只能从情理上做出分析,并把分析的依据主要放在直接记述叔梁纥求亲的《孔子家语·本姓解》之中。
叔梁纥以正规的士人之礼迎娶颜徵在为妻至少有三方面的困难。首先,根据《孔子家语·本姓解》的记载,当叔梁纥求亲于颜氏之时,已经育有九女一子,根据当时的婚姻习惯,他的年龄应该是在四十岁左右了。而颜氏有三女均未出嫁,颜徵在又是三女中最小的一个,年龄应该在二十岁以下。这种年龄上的差距,应该是第一项困难。其次,《孔子家语·本姓解》并没有交代为叔梁纥生下九女的原配之妻是否在世,如果其妻在世,叔梁纥主要是为了生儿子而寻求婚姻,这应该成为第二项困难。最后,自孔子五世祖木金父从宋国迁居鲁国以来,
经过四代人的经营,还有两代人做到了邑大夫,这个家族恐怕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在这种形势下,叔梁纥虽为家族首领,但在婚姻大事上,或者因为上述两项困难,或者与家族沟通不够而遭遇到家族的阻力,这有可能成为第三项困难。面对上述困难,虽然《本姓解》说“遂以妻之”,认为叔梁纥娶颜徵在为“妻”,但在事实上,很可能“妻”的称号只是双方私下的约定。因为只是私下约定,当然就无法举行各方认可的正式的婚姻仪式。所以,《史记·孔子世家》的“野合”之说,是说叔梁纥娶颜徵在为“妻”,只是事实上的妻,而不是符合礼仪之妻。
从结果上看,无论《史记·孔子世家》的“野合”之说是否有根据,叔梁纥最终是与颜徵在生活在了一起。从颜父征求三女意见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颜徵在显然是一位有主见的女性。所以,在进入叔梁纥之门以后,《孔子家语·本姓解》记载说,颜徵在清醒地意识到,当务之急是要为叔梁纥生育一个男孩子。这一想法既是叔梁纥娶妻的初衷,更是考虑到叔梁纥年龄偏大,生育后代,还要生育男性后代,都是比正常情况下更为困难的事情。为此,颜徵在私下里去了鄹邑城外的尼丘山,祈祷神灵赐福给她,让她早日实现丈夫的意愿。颜氏此举当然是受到了当时风俗的影响,尽管此后不久颜氏就生下了孔子,并因为祈祷于尼丘山而以“丘”字为孔子之名、“仲尼”为孔子之字,但从现代人角度来看,那也只是一种有益的心理慰藉而已。古人的名与字之间一般都有联系,尼、丘二字与尼丘山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究竟是因为“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的原因,还是仅仅因为尼丘山位于鄹邑城外的原因,后人也不必一定要寻求一个肯定的答案。另外,因为孔子有同父异母之兄孟皮,所以取字仲尼。孟、仲是古人为家中之子排序的用字,孟或伯为长子,仲或叔为次子,季则是指三子。那时的人尊称有地位或有德行的人为“子”,所以,“孔子”一名更见流行。
综合上述,孔子的出生,显然是个困难重重的过程。孔子是父亲朝思暮想的儿子,但偏偏是父亲年长之后才出生。孔子的母亲并不是父亲的原配之妻,这在那个时代有可能对一个人形成终身的影响。《论语·八脩》记载说,孔子的敌手们称孔子为“鄹人之子”①,这是一种明显带有歧视的称呼,暗示孔子的出身是有某种公认的污点或不足之处的。尽管孔子很好地把这种舆论的不利压力转化成为自己不断上进的积极动力,但这种无妄的困难始终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
孔子的出生地是鲁国鄹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东南尼山附近),时间是公元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但也有记载认为,孔子是公元前552年所生。历代有许多学者为此而各执一辞,聚讼不已。在这个问题上,或许钱穆的意见更为平和,他说:“今谓孔子生前一年或后一年,此仅属孔子私人之年寿,与世运之升降,史迹之转换,人物之进退,学术之流变,无足轻重如毫发。”
孔子虽然是幼子,但并没有享受到父母的百般宠爱,因为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在孔子很小的时候就亡故了。《史记·孔子世家》说:“丘生而叔梁纥死。”《孔子家语·本姓解》说:“孔子三岁而叔梁纥卒。”总之,孔子对父亲并没有深刻的记忆,自然也难以体会真正的父爱。
叔梁纥去世后,孔子与其母颜徵在的生活情形已无史料可证。可以稍加推测的是,颜氏是鲁国的望族,母亲颜徵在带着孔子来到当时鲁国的都城曲阜,在颜氏家族中生活的可能较大一些。这在一方面有生计上的考虑,再一方面,如上所言,以“野合”的方式进入叔梁纥家中的颜徵在,在叔梁纥去世后,很难想像会得到这个家族的精心庇护。不过,在孔子时代,颜氏家族已不属于富贵阶层,以贫居著称的孔子高足颜回就是其中的一员。幼年的孔子虽然有母在侧,但生活之艰辛依然可想而知。孔子成年后自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便可证明其年幼时的困顿生活了。所谓“少也贱”,是说缺乏深厚的家族背景,没有像样的社会地位;所谓“多能鄙事”,是说必须从事低级的劳动来谋生。
颜徵在可能在孔子成人之前就亡故了,相信这对孔子的影响很大。成年后的孔子(至少从记载上看)从未提及自己的父母,这当中有种种可能,而最大的可能是父母均在他能够记事的年龄之前便已谢世。也有可能是,后亡的母亲极为普通,虽然生养了孔子,但并未给过他令人印象深刻的培养。孔子甚至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意思是说,那个时代的女性是难以相处的。理由是,如果亲近她们,她们就会桀骜不驯;如果疏远她们,她们又会怨声不断。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如果他的母亲是让他记忆深刻的超乎寻常的女性,孔子自然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来。当然,无论实情如何,立足今天的我们,还是可以说颜氏称得上是位伟大的母亲。她不仅生养了孔子这样的伟人,还能在那样的逆境中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并使孔子能在颜氏这样的大家族中获得成长。如上所言,虽然这并不是一个显赫和富有的家族,但历史悠长的家族中总有些通晓世故、明于礼义的德高望重者,怜悯这个聪颖的孤儿,教以书契礼仪。这使孔子从小就对传统文化有了相当的认知和较深的熏习了。
传统,毫无疑问地会使一些人背上沉重的包袱,窒息了他们的创造性。然而,孔子却无疑属于既能遵循传统,又具有创发性的出类拔萃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好古”和“敏求”。童年的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②,即使是在游戏的时候,也许只有些砖头瓦块,孔子并不像普通孩子那样扔来扔去、打打闹闹,而是认真地模仿成人的祭祀活动,摆好供品,神情严肃地完成各项礼仪。类似这样的表现,在孔子的童年时代肯定不止于这种模拟。这就说明,孔子确实生活在一个有规矩有教养的环境中,虽然他的“玩具”是简朴的,比不上贵族子女的奢华,但他的表现却是高贵的,是那些轻视传统的贵族之家无法比拟的。这种对传统文化的遵从和实践,既显现出了孔子的天赋,又证明了传统教育在他身上得到的回应。
第三节 青年求学?使命在肩
少年时代造就人的性格,青年时代决定人的志向,因为性格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而志向则需要经历一些值得让人回味和思考的事件,也需要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时代有相当程度的观察和感知。在孔子的自述中,从少年立志于学到三十而立后的独立思考,有十五年的时间。史籍中对于孔子这十五年中经历的事件记载较少,原因之一,可能是这段时间内与孔子交往的人多半未能经受得住历史的冲刷,没有留下多少历史痕迹。尽管如此,那记载不多的几件事,已经足以让我们了解孔子为何会立下治国救世的远大志向。
个人生活如前所述,孔子三岁时父亲去时,葬于防邑之外的防山。但由于当时孔子年纪太小,对父亲的埋葬之地并没有印象。孔子长大之后,母亲由于不受丈夫家族的容纳,也就不愿意向孔子提起他父亲的事情。想像孔子也应该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既然母亲不主动提及,他也从不打听。童年时专心于“设礼容”之类的成人般的游戏,少年时则“志于学”,一门心思地学习。就这样,当母亲去世之时,孔子都无法将从母亲与父亲合葬。只是在好心人的指点之后,孔子才将父母“合葬于防”。至于母亲何时去世,典籍并无明确记载。从《孔子世家》的记载顺序来看,应该在孔子十七岁之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很早就成为孤儿的孔子,所能做的事情,除了通过劳动维持生计之外,应该就是读书求师的生活了。
经过初步的学习,青年时代的孔子满脑子都是整治天下的雄图大略,但在这个时候,他的个人生活情形,除了《孔子家语》所载的一些颇有争议的说法而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孔子家语·本姓篇》说,孔子十九岁时迎娶宋国的亓官氏之女为妻,次年得子,取名鲤,字伯鱼。孔子还有一个女儿,想必也是这位夫人所生。伯鱼既是孔子的至亲之人,也是他的学生。伯鱼先孔子而亡,也不存在传承孔子之学的问题。且从《论语》记载的情形来看,伯鱼也算不上是孔子的杰出弟子。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