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克服明清的具体乡约形式中削弱和损害乡约精神的那种消极因素,就需要有个人自由。就如下述引文清楚阐述的那样,这种转变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要像我们前面引述过的那种方式一样,抛弃其传统的个人/社会关系模式,而只需以兼容的方式补充之:
现在是中国人很苦闷的时候,是在一个左右来回的矛盾中。这就是说:中国人一面散漫缺乏团体组织,同时还缺乏个人自由平等的确立,两者都是急待充实。但是如果注重自由平等的一面……则让我们很难照顾团体结合的一面,将使中国人更加散漫。照我们刚才所讲的团体组织,其组织原理就是根据中国的伦理意思而来的;仿佛父子、君臣、夫妇、朋友、兄弟这五伦之外,又添了团体对分子、分子对团体一伦而已。……
(本来在乡约中对于各种事情,也都照顾得很周到……)不过所差的只是一点(消极);我们则是把消极的相体恤,变为积极的有所进行。中国古人对于生活的方法上,不大十分讲求进步,如:有手推车、牛马车,即不讲求汽车、火车,这种态度在乡约中也看得出来。我们则把他改为积极,在积极的进行中即包含了讲求进步
之意……如果梁漱溟认为西方的群体组织方式提供了——实际上是要求——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那么中国之所以需要这种自由,是因为过去阻碍了中国的那种个人主义事实上是有限的。那种个人主义,按他的说法,是根据静态的角色和关系、根据一套规范——这套规范不承认“善是无止境”——而界定的。它的仁或人性概念需要以一种更加宽泛的社会事业(social enterprise)的观念来表述。在下文中,梁漱溟指出了传统乡约的局限,但无疑他也在思考新儒家的修身这一模式,该模式的极致就是《大学》中的“止于至善”,而且到了“止于至善”的境界,也就圆满了;也就是“中庸”。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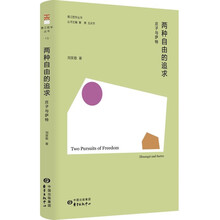







——Daniel A.Bell,清华大学
(狄百瑞)此书精辟地反驳了那种认为以孔子的《论语》为基础的“亚洲价值”与西方的人权模式不兼容的观点……该书智见充盈,学思激荡!
——Arnold Beichman,胡佛研究所
狄百瑞与那些利用儒学来论证威权主义之正当性的人针锋相对,他颇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儒学中的因素具有内在的潜能,可以演进为民主政府。他以其深厚广博的儒学知识,生动地描述了一系列的儒家价值与儒家措施,它们有可能滋养催生出一种现代自由主义。
——Merle Goldman,波士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