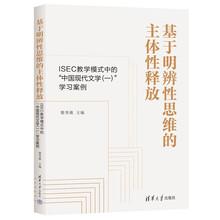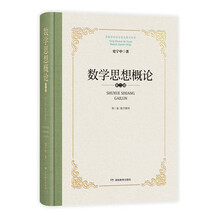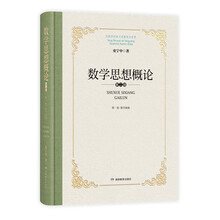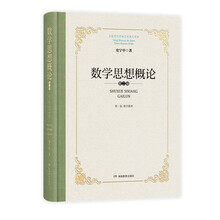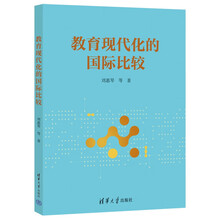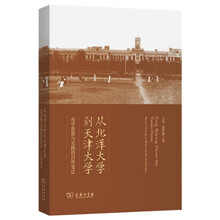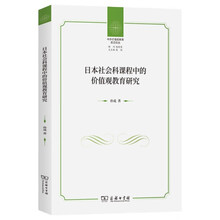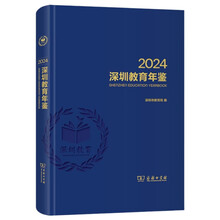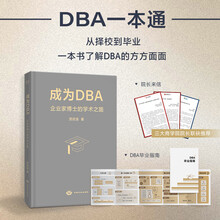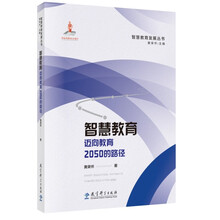第二,以对受教育者的强制服从为手段,使教育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在以人的依赖性为标志的生存方式下,政治是社会的核心,教育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属物。群体道德以对个体生命与尊严的漠视实现自己的崇高,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军事暴力外,教育是其最为得力的助手。教育实现这一期望的妙方在于:对个体施加生理与精神的强制,使其心悦诚服地接受群体道德的奴役与控制。①这种无视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目标的现象在中外一直占有统治地位,而且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在西方古希腊的斯巴达、雅典教育、古罗马教育和中世纪的经院教育,其唯一目的是通过教育培养顺从统治阶级的人才。在中国从奴隶社会的“六艺”教育,到封建社会的“五常”教育,无不渗透着违背教育自身价值的气息。这种把教育的目标定位于为统治阶级服务,无疑存在着教育善恶问题。
第三,以受教育者处于教育的从属地位为特点,使教育成为政治的附属物。在中国早期教育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小生产的农业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所以伦理秩序成为维系农业社会的根本,伦理关系直接表现为政治关系。反映在教育过程中的伦理关系也是一种政治关系。天、地、君、亲、师并为人极,教师成为“道”的直接体现,是政治关系的代表。教育为政治服务成为首要的任务并表现为建立社会的伦理秩序服务。培养学生的目的在于培养一个适应社会伦理秩序的人。在西方社会,教育成为宗教的依附品,成为宗教所代表的群体主体的工具,从而失去了教育的理性尊严。虽然它所从事的是培养人的理智工作,但这像一个失去自由与理性的人一样,是无法谈及本身的道德的,因为他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当教育活动本身没有自己理性与自由,所谓的教育道德便只是一种社会道德的镜像而已。②
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教育也进入到了飞速发展时期。各种教育改革不断进行,各种教育思想不断涌现,教育成为商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