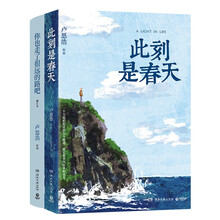一年之祭
雨停了吗?一夜狂风乱吹,和我一年前独自秉烛的一晚相似。
窗外夜色中一户人家的灯光,和一切不为人知的往事一样,都在梦中。
重复是可怕的,它消磨了意义,是谁也这么说过。
终于放至临死时想说的话也可以不说了。
和SOSO在公司的地毯上长谈的,再也没有兴致去说。时间之土不厌其烦的把坑填成一个滞纳的平面。
SOSO的故事依然在继续着。
她在等待着四月之末的他的答复。
四月之末,没有诗人写过四月之末。
而人们是否永远没有理由悲伤?
时间如雨水冲蚀铭文,更为简单的是,一些东西消磨在入夜进至黎明的过程中,起初站立的方向在酒醉后磅礴的泪中以及此后不安的睡眠中滑人了无意义。
可是曾几何时,那样坚定地说不想清醒于荒诞玩弄于荒诞,说不想被时间和理性否定了当时的疼痛。
可,什么样的疼痛会继续?
行将四月之末,一年以前SOSO尚在日本,信中讲述她的故事,那信在今年三月的某日夜晚重又读来,仍如当时一样,让人觉得远了。那阵子,我总在深夜给SOSO回信,那些日子常在午夜之后,独我秉烛时下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摇曳的烛光暗明的屋子里,磅礴的雨声如放我一人听。
今日,且让我重忆起当年的信,以为一年之祭。
3月25日
SOSO,读完你的信,所有的感觉逼迫出一句话:我是最浪漫的倾听者。想象你我之间隔着一盏台灯,我如现在这般坐卧在床,侧脸对你,听你说话,我是最浪漫的倾听者。
许久以后,在听你诉说你的故事时,我仍可以保留着我想象我所有的最浪漫的姿态。
这几日,天色阴郁,天很矮,在白天,天就泛出发黄的照片般恹旧的光,此刻仿佛泄入纸上。一张白纸,几行疏散的字,还有那隐秘的光。一时,往事似乎远了。
崔健在唱:“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
在爱中成熟起来的女人更有理由做到坚强,坚强真美,彻骨的干净,可惜我所想的寥寥,但你不同,坚持吧,祝你幸福。
夜即降临,天外青灰,有人家点起灯火,窗外转瞬便能全黑,我更想多留住一点现在的时刻,窗外有天,有交错的层次感,有风景。留我一人在寝室,当有人转身出门的时候,我不禁泪流,我何故让自己相信只有你最体谅我的伤感。
是否歌词也写过大致这样的意思,不再写信并不表示不再思念,不再时时想起也并不表示忘记。
只是一时猛烈干净的挚性似乎久违了,今晚重新翻来,任它泪流,这里无人。不能再细想那夜,你念了我给你的信,我紧握了你的手,我们喝酒,你能与我痛哭。
正大大动情如你,得此深爱,我也欣慰。
4月4日
收音机里任何一个旋律的低音,都是我现在嗑瓜子的姿态。
今天是4月4日,我的上封信你快收到了。放目窗外的天,多云的天,现在虽没有金色的阳光,但天还是高了,亮了,凝神望去,仿佛可以和你离得近了。想到你很快就可以念到我的信了,这给我人群中寞寞的心一点安慰。
想念你的语气还有你的一声叹息。想象你此刻突然夺门进来,短促地唤我一声NONO——
我一定热泪如注。
一段时间未给你片言只语,当时我不担心你恼丧,只想只等见面时便能彼此明白。我自语,太多的话等你回来以后再说,再多的事见面时就都会知道。
你来信写我的只有几句,“我相信这丫头会有惊人之举,”“这也才是她才可做得的事”……这几句也让我知足了,并不因为他们说得对。你偏袒得让我心酸。
别太相信了我的伤感,它们果真是有或有过,只是在这时才被恣意地渲染了,就像一个孩子受了委屈对母亲哭泣时的一点放肆矫情与更加的委屈。
收音机里在放一首简单平快的二拍子的通俗歌曲,节奏真飘扬。
一年过去了,为什么很多事都在雨夜里发生,何曾相似又何曾不同。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而据说雨水只懂得流淌却不懂得积累。
是否我们永远没有理由悲伤?
故事片里一个女孩哭泣着在课堂里念一首诗:“再也没有灿烂的阳光壮美的草原鲜艳的花朵,没有悲伤,我们只有从现有的一切汲取力量。”
很多事都以喜剧而告终。
纵然如今,我们已不再都以里尔克致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中的第七封信而共勉。
但毕竟,我们曾在宿舍的黑夜里共同听收音机中乔榛用厚重的嗓音朗诵两句普通的诗行:“被人爱是多么幸福啊!有所爱是多么幸福啊!”
我记住了有朋友在他的小说的结尾处写道:“假如有人问我的名字,我决不说,我决不说。”
然而,又有什么可以说出口。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