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一直以“理性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形象,但这一形象在18世纪受到浪漫主义的严峻挑战。从此,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争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内在张力,影响着西方哲学的自我认同,导致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分裂。罗蒂汲取了黑格尔的教训,以偏向浪漫主义的姿态,对两者加以改造和重新安置,对什么是元哲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西方哲学的当代分裂
在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降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哲学从来没有遇到过今天这样的危机。在过去的岁月中,虽然有过中世纪对神学的依附,但西方哲学家们仍然可以在经院内运用理性围绕着神学的话题交流各自的观点,讨论实在论、唯名论的孰是孰非。哲学家之间起码的协同感(the sense of solidarity)并没有丧失。然而这种状况在20世纪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哲学家阵营开始分裂,英美分析哲学家和欧洲大陆哲学家行同路人,彼此不了解对方,也不明白对方在做些什么。分析哲学家们既不懂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在说些什么,也没有兴趣读他们的著作;同样,大陆哲学家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必要去研读罗素、卡尔纳普、奎因或戴维森,对那种把哲学符号化的做法更是感到从未有过的陌生。就像罗蒂所说的,能同时在两个阵营之间游刃有余的哲学家并不多见。①
应该说,同一学科下的不同分支之间,彼此不了解、不明白对方的工作性质和意义,这种情形十分常见。天体物理学家未必懂得物理化学家在说些什么,经典物理学家未必懂得量子力学家们在说些什么,大脑神经学家未必懂得细胞蛋白质学家在说些什么。但科学家们似乎没有为此感到焦虑,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些彼此之间的隔膜,并不影响他们对科学自我形象的共同理解。当代哲学则与此大不相同。在英美哲学家眼里,海德格尔、德里达无异于江湖骗子,说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语言,满足人们对神秘感的迷信;而在大陆哲学家看来,英美的分析哲学家们已经将哲学引入歧途,使其堕落为一种小打小闹的技艺,一种烦琐不堪、不值一提的小玩意儿。②他们彼此对对方的工作嗤之以鼻。何以至此?答案是:在他们各自的心目中,有着一幅互不相容的关于哲学应该是什么的图画。换句话说,他们在元哲学层面上,在哲学观上有重大的分歧。我们不应该对哲学家们的真诚有任何怀疑,他们献身哲学的激情毫不逊色于他们的前辈,也毫不逊色于和他们同在一个学校的物理学系或化学系的同事们,他们之间的战争涉及到一个严肃的话题:什么是哲学?
英美分析哲学家眼中的“哲学”始终和科学形象连在一起。自然科学的进步和成就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追求精确,重视论证,是他们所崇尚的风格。在他们看来,哲学应该效仿科学,澄清知识结构,展示知识要素之间的关系,一劳永逸地在知识和谬误之间划出牢靠的界限。而大陆哲学家则对哲学的科学形象毫无兴趣①,他们更愿意从文学那里汲取哲学养料。“真理”不是他们所热衷的话题,他们的“目的是保证谈话继续进行,而不是发现客观真理”②。他们并不对如何准确地映现世界感兴趣,而是对如何为我们的旧语汇增加新词,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感兴趣。
因此,罗蒂更愿意用“对话哲学”而不是“大陆哲学”来概括这一哲学倾向。应该说,“对话哲学”比“大陆哲学”更准确地揭示了与分析哲学相对立、当下在欧洲大陆流行的哲学的特征。
当代西方哲学的分裂折射出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由来已久,今日西方哲学的分裂,其实早在18、19世纪的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战争中埋下了伏笔。
(二)理性主义及其困境
在西方哲学界,长期以来,理性主义一统天下。它的基本特征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已经得到清楚的表达。以塞亚?柏林把这种理性主义传统看作是西方文化的特征,认为它主要由三个支柱所支撑:第一,所有真正的问题都能得到解答,无法得到解答的问题,必定不是真正的问题;第二,所有的解答一定是可知的,是可以学习、传授的,并且存在有一种可被学习和传授的技巧,人们借此寻求答案;第三,所有的解答一定是彼此互容的,它们融会在一个大写的真理之下。③
这种理性主义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一般预设。它不仅是哲学的骄傲,也是西方文化的所需。理性化程度的高低,逼近大写实在的距离的远近,成了文化各部门有序排列的根据。目标坚定而又明确,“真理”作为耀眼的灯塔,指明了人们前进的方向。
柏林认为,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的这种理性主义模式主要来自于希腊人对数学、几何学的推崇。
相信世上存在一种完美的前景,相信只需借助某种严格的原则,或某种方法就可达到真理,至少这是与冷静超然的数学真理相似的真理——这种信念影响了后柏拉图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他们认为有可能——如果不是绝对的话——达到某种近乎绝对的真理来整饬世界,创造某种理性秩序,由此,悲剧、罪恶、愚蠢,这些在过去造成巨大破坏的事物,最终可以通过应用谨慎获得的知识和普遍理性得以避免。①然而,柏林提醒人们,必须警惕这种理性主义幻象,因为它容易背离自己的初衷,导致对人的奴役。毫无例外,这些模式的初衷是要将人类从错误中解放出来,从困惑中解放出来,从不可认知但又被人们试图借助某种模式认知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但是,毫无例外,这些模式的结果就是重新奴役了解放过的人类。这些模式不能解释人类全部经验。于是,最初的解放者最终成为另一种意义的独裁者。②
怎么理解柏林所说的理性对真理的追求会导致新的独裁呢?我想,可以有这样几个解释:第一,就像柏林自己上面所说的,“这种模式不能解释人类全部经验”。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是否要运用希腊人所推崇的那种理性模式来解释世界、安排人的生活,是不确定的。有些文化,比如犹太文化,其信念主要来自于家庭生活,来自父与子的关系,人们据此来解释自然和人生,这在希腊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再比如中国传统的非线性的阴阳辨证思维方式,由人伦推及宇宙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等,也不同于希腊理性的思维方式。如果只有理性的方式才能把握真理,则所有这些思维方式都应该被放弃。第二,从存在主义的视角看,当我们在人那里找到作为其本质的理性,并把人的使命定为运用这一理性达到大写真理的时候,我们无异于把人降到了物的水平,使人变成了一种受奴役的存在者。物和人的不同在于,它在存在之初已经被规定了本质,它受这种本质的制约,并无自己的存在。桌子的本质是什么,早在桌子存在之前已经被确定了。而人不是这样的,人存在着,不断地选择着、创造着,直到死亡,才能“盖棺论定”。当我们说人有一种本质,叫理性,其天命是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逃避选择,逃避自由,好像有一种强制力,促使着我们朝向一个目标,抗拒它就是抗拒真理、抗拒过人的生活。第三,如果说真理是信仰的结果,那么我们还可能有别的信仰的余地。但如果说真理是每一个有理性的人,运用其理性必然要承认的东西时,它就获得了一种无比强大的威力。不接受它,就是故意闭起眼来敌视真理,这样的人,要么是精神有问题,要么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阿奎那要用理性来证明上帝,也就不足为奇了。理性以及作为理性之目标的真理,具有一种强制力,一种一体化的强制力。个人在它的面前是软弱无力的,笛卡尔、康德都崇尚理性,要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思考,“敢于运用你的理性”成了启蒙运动最响亮的口号,然而,如果这种理性只是我们共同拥有却又只能服从而无法改变的宿命的话,个人就只能是理性实现它自己的奴隶。人从上帝那里解放了出来,但又重新被自己的理性所奴役。
正是出于对理性主义这种负面效应的反抗,我们看到,在启蒙运动倡导理性主义之后不久,西方的思想舞台上,一个新的角色登场了,如果说,在启蒙运动那时,是上帝和巨人之间决斗的话,那么,这个新角色的使命,就是要在巨人打倒上帝之后,对巨人本身进行挑战。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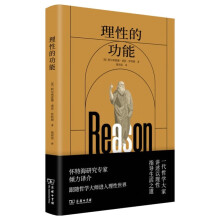






——蒙蒂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