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学当中最重要的问题,直到十分晚近的时候才被许多科学家当成科学研究的一个适当主题。这个问题是指:大脑中的神经生物过程究竟是怎样引起意识的?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各种刺激物——例如当我们品尝葡萄酒、遥望天空、闻玫瑰花、聆听音乐会时——会引发一系列神经生物过程,这些生物过程最终会引起统一的、良序的、融贯的、内在的、主观的觉识或感知状态。现在的问题是:在上述刺激物对我们的接受器形成刺激和我们的意识经验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间的过程究竟是怎样引起意识状态的?再有,这个问题不仅关涉到我所提到的感知的情况,还包括自愿行动(action)的经验,以及像因为收入税问题而感到担忧,或者设法记住你岳母的电话号码等这样的内在过程。下面这一点就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我们意识生命中的每一件事,从感觉到疼、痒和瘙痒到——挑你最喜欢的说——感觉到后资本主义下后工业社会中的人的焦虑,或者是经历厚雪中滑行的心醉神迷,这些都是由大脑过程引起的。据我们所知,这些相关的过程发生在突触、神经元、神经柱和细胞结集的微观层次上。我们的所有意识生活都是由这些低层次过程引起的,但是,它们是怎样运作的,我们却只有一点儿模模糊糊的认识。
当然,你可能会问:有关专家为什么不继续做这项研究,直到把它们怎样运作这一点搞清楚呢?为什么这件事会比找到癌症的起因更困难呢?但是,存在着很多特殊的特征,使得脑科学提出的问题更难解决。其中的一些困难是实践层面上的:按照当前的估算,人脑中有超过一千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又都和其他神经元(从数量上看,少则几百个,多则数万个)由突触相连接。所有这些极为复杂的结构堆在一个比足球还小的空间里。再者,如果我们不破坏大脑中的微量元素,或是杀掉大脑这个组织,那我们便很难去研究大脑中的这些微量元素。除了这些实践层面上的困难,还存在着几种哲学和理论上的障碍和混淆,使得我们很难提出和回答正确的问题。例如,我用来提出“大脑过程怎样引起意识?”这个问题的习以为常的方式,从哲学上看就已经有很多意思了。许多哲学家,乃至有的科学家都认为,大脑和意识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因果性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承认它们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就意味着接受关于大脑和意识的某种版本的二元论,而这是他们希望基于其他理由加以拒斥的。
从古希腊到新近关于认知的计算模型,关于意识以及意识和大脑之关系的整个主题已是混乱不堪了,至少,该主题发展史上出现的一些错误,会在近来对我要在本书中讨论的主题的考察中重新提到。在讨论最新研究成果之前,我想先澄清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并纠正一些在我看来最严重的历史错误,借此来设置讨论的平台。
有一个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这是一个被认为很困难,但在我看来似乎并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即对“意识”进行定义的问题。给这个词下定义被认为是极端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区分了分析性定义(其目的在于分析一种现象的根本性质)和日常定义(只是要确定我们正在谈论什么),那么,给出这个词的日常定义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困难:“意识”就是指这样一种感知和觉识状态,当我们从一次无梦睡眠中醒来,直到再次入睡,或者陷入昏迷,或者死去,或者变成“无意识”时,就会有这种状态。梦就是意识的一种形式,不过它肯定和充分清醒时的状态很不一样。如此定义的话,意识就是时断时续的。从这个定义看,一个系统要么是有意识的,要么不是有意识的,但是,在意识域内,存在着从昏昏欲睡到完全觉识这种强度状态上的变化。如此界定的意识是一种内在的、第一人称的、定性的现象。人和高等动物显然是有意识的,但我们并不知道意识进化到了什么程度。例如,跳蚤有意识吗?就神经生物学知识现状而言,为这种问题操心可能没有什么价值。我们没有足够多的生物学知识,以致能够知道进化会在哪里终止。另外,意识这种一般现象也不应混同于自我意识(self-一consciousness)这种特殊情形。最有意识的状态,如感觉到疼,并不必然涉及到自我意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一个人会意识到自己处于某种意识状态之中。例如当一个人因为自己过度担忧的倾向而担忧时,他就有可能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积习成癖的担忧者,但意识本身并不必然蕴涵自我意识或者自我觉识。
第一个正式的问题来自于理智发展史。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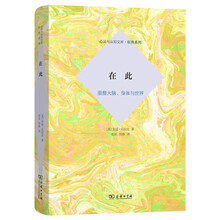






——柯林·麦克金(Colin McGinn),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