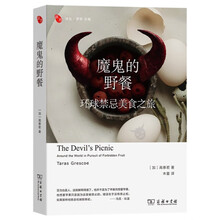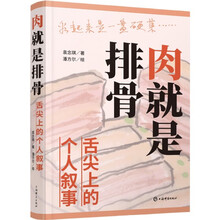春秋时期,诸侯弃酒礼于不顾,史籍多有记载:《左传》襄公三十年:“郑伯有嗜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至未已。”《晏子春秋·谏上》:“齐景公饮酒七日七夜,不纳弦章之谏。”《新序》六:“赵襄子饮酒,五日五夜不废酒。谓侍者曰:‘我诚邦士也夫,饮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优莫曰:‘君勉之,不及纣两日耳。纣七日七夜,今君五日。”’优莫还讽谏他说:“桀纣之亡也,遇汤武,今天下尽桀也,而君纣也,桀纣并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足见此风之盛。<br> 按照古礼,夜饮为淫乐。饮酒夜以继日,礼崩义废,证明新的道德生活方式还没有在社会生活中确立起来,无怪儒家忧心忡忡。社会上层腐化如此,民间酤饮亦无禁忌。这时“工商食官”的旧体制已经瓦解,私营工商业异常活跃,酤酿求售便是其中一个重要行当。《诗·小雅·伐木》:“有酒渭我,无酒酤我。”《韩非子·外储》:“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都是反映这方面情形的有力证明。<br>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面对新的社会状况,孔子思想中不可能不有所反映与触动。一方面,科技进步不可能逆转;另一方面,嗜酒之风需要节制。值得注意的是,经孔子删削整理的六经中,没有提到“仪狄作酒”和“禹恶旨酒而好善言”这个绝对禁酒的故事。但孔子不著录这事的原因,似不在于不语“乱、力、怪、神”,而在于孔子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白酒问事以来,酒行为便成为一种社会存在,有其延续的合理价值。一味禁戒不是办法,也无从办到。况且,肇乱之源并不在于酒本身,也不丰于饮酒行为之中,而在于人欲贪婪和无节制的滥饮。上古那种相当绝对的禁酒办法与“中庸”之道不合,已属相对落后。改良的办法是要规定一些具体的道德约束和礼仪制度,循循善诱,进行自我约束,辅助酒禁的实施,因而孔子提倡酒德是很自然的事情。<br> 禁酒之教,是上古农业文明的遗产。孔子和儒家文化并没有抛弃这一点,而是将它与酒政管理结合一体。几千年来,酿酒业在小农经济的制约下,始终和民本(人口)问题、粮食问题以及天灾人祸相冲突。人多粮少,神多酒稀,不酿不祭不成,滥饮不禁也不成,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只能是禁酒原则指导下具体的酒政措施。儒家赞赏的酒政管理,体现在《周礼》一书中。《周礼·秋官》有萍氏之职:“萍氏掌国之水禁。几酒、谨酒。”几(讥,通稽)酒即“苛察沽买过多及非时者”,“使民节用酒也”。这与《尚书·酒诰》中“无彝酒”的要求相符合。<br> 《周礼·地官》司市下设司蔬一职:司■“掌宪市之禁令,禁其斗嚣者、与其虢乱者、出人相陵犯者、以属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这与“执群饮”的禁令也相吻合。<br> 萍氏、司■,都是对付民间饮酒的,贵族统治者自己则设酒官,有限度有节制地供给王室和大臣们用酒。《周礼·天官》特设酒正一职:“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为公酒者亦如之。”式法是作酒的程式方法,授酒材是授人以粮食、曲蘖之类的制酒原料。为公酒者,指为公事而作酒,必因有事而授酒材,故亦称之“事酒”。酒正为酒官之长,属下还有酒人、浆人等:“酒人掌为五齐三酒,祭祀则共奉之”,“浆人掌共王之六饮”。酒官之设,是与“饮睢祀”、“禁沉湎”的原则相一致的,可见命意之深。<br> 总之,孔子和儒家的“酒禁”、“酒政”观念都要求官员和民间都节制酒的消费,而非完全断酿酒、饮酒。孔子终究懂得,酒是一种双重事物,“本为祭祀,亦为乱行”,虽可“起造吉凶”,但“德昏政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事。所以他在《大戴礼记》中又说:<br> 公曰:“所谓失政者,若夏商之谓乎?”<br> 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夺之魄,不生德焉。”<br> 公曰:“然则何以谓失政?”<br> 子曰: “所谓失政者:疆蒌未亏,人民未变,鬼神未亡,水土未姻;糟者犹糟,实者犹实,玉者犹玉,血者犹血,酒者犹酒。优以继堪,政出自家门,此之谓失政也。非天是反,人自反。臣故日君无言情于臣,君无假人器,君无假人名。”<br> 公曰:“善哉!”<br> 这样外貌安然,上下逸乐,继之以忍,“政出自家门”,“非天是反人自反”,是其所以失政的根本原因。但毕竟“酗酒废政”是为孔子所鄙薄的事情,这里既含有对酒的谏诚,也含有对人的指责。孔子和儒家伦理哲学的核心是“仁”和“礼”,酒德和酒禁体现了一个“仁”字,而酒礼则直接出于《周礼》。<br> 孔子与儒家的酒文化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汉以后,统治者以孔教为正统,士人对儒家经典十分追恋,十分迷信。无论是研究各代政策制度的专著《文献通考》,还是荟萃百家之言的巨典《古今图书集成》,记酒事均先就《尚书》和《周礼》说起,“几酒”、“谨酒”、“礼酒”的原则长时期内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从而将儒家的酒德观念抬高到中国酒文化体系中的显赫地位。<br> 自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初榷酒酤”以来,一种新的酒政思想(榷酒、税酒)开始抬头,并向儒家的酒德思想提出挑战,禁酒和榷酒成为历代频繁争论的重大理论问题。主张税酒、榷酒的人大多基于国家财政观点,而主张禁酒政策的无一不是追随孔子之说。从国家财政的实际出发,酒税、酒利难以割舍,因而酒税、榷酒政策历代均有保留,在实践中直接为治人者所用。然而酒礼、酒德、酒禁的思想,借助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在意识形态和上层领域却有广泛影响,特别是当“年荒谷贵”,“民食匮乏”之际,更直接转化为政策禁令,屡屡获得实施,因而禁酒的记载,历代也史不绝书。<br> 苏轼、邱浚和顾炎武便是后世提倡儒家酒德文化比较典型、比较著名的几位人物。宋代苏轼是反对新法中确立理财观点,推崇周公禁酒正德的。他说:<br> 自汉武帝以来至于今,皆有酒禁,严刑重赏而私酿终不能绝。周公独何以能禁之?曰:周公无所利于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责之学,乙笞其子而夺之食。此周公之所以能禁酒也。<br> 苏东坡他不只反对榷酒病民,夺人之食,进而宣扬“重德教轻功利”,维护“先圣”禁酒之训。这一点,他的弟弟苏辙说得更明白:“故世之君子,能观《既醉》之诗,以和平其心,而又观夫《抑》与《酒旖》之篇,以自戒也,则五福可以坐致,而六极可以远却。而孔子之说所以分而别之者,又何足为君子陈于前哉!”<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