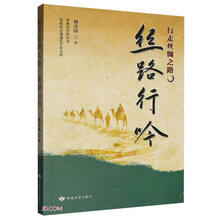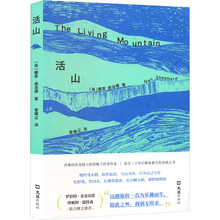一、我的朋友老布
我在休斯顿的生活,就跟休斯顿每天的烈日一样简单:日子按交作业和考试的期限划分,走路的距离限于家到学校的科学楼和图书馆,机房。连电视都没有的寓所里,一个中国人每日耐心地睡觉,起床,煮米饭。
不过生活也有另一种划分法:有时一个人突然跟我发生关系,日子也随之涌来活水。原来自己过着多重生活。现在降临我身边的是德国人布克斯特胡德。几日来很巧地不断听到他的作品的演奏会和讨论会,关于他的资料和录音接二连三飞到我手上。轻躺在床上的时候,CD机里也总是他的声音,丝绸一样的管风琴声。这个人我深爱多时,几乎像爱巴赫。我的生活在他的音乐里,也像丝绸一样被揉捻,欢喜地抖动。
其实情牵总是瞬间的事——那天管风琴老师送我一张他录的CD,开篇就是双管风琴演奏的老布,那是BuxWV155,d小调托卡塔。开头的音阶过后,开始了细细的托卡塔,攀爬的形状像锋利的岩石边缘。抬眼环视天花板之间,老布跟我的缘分瞬间锁定。我仰面躺倒在床上,胡思乱想的都是有朝一日我也在音乐会上弹这个人的曲子,让那丝绸和潮水一样的幻想在音乐厅里奔涌,吞噬掉一颗少年心,哪怕只有一颗。我要把那孩子夺过来,在教堂和管风琴的幻象和“妖氛”中重铸魂魄。那岂不妙哉。
布克斯特胡德,生于1637年,比巴赫早五十年,早得连画像都不存,连确定的谱子都不存。如今大家对着让人将信将疑的谱子争个没完,给学术刊物和会议带来无穷的话题和论文。老布如果在世,自己也会将信将疑的。他的曲子往往在岁月里慢慢生长,跟他自己的生命一道变化长熟,自己其实也握不住走向。
虽然后来成了北德意志管风琴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布其实生于丹麦(后来那小城归了瑞典),老爹就弹教堂礼拜,他没上过什么学,二十多岁承了父业,一古脑儿在教堂弹了四十年。父子兵主宰小城的音乐生活,慢慢享受着几乎不被挑战的名声。呵呵,既然我们不知道什么具体的故事,就当他们果然成功得圆满好了,而且生活里没有波澜,快乐得完美。也许这都是真的。这个老家伙在音乐上哺育了巴赫,如今我拿着两人的乐谱慢慢比较,竟然发现老布常常更高更难。我曾经那么耐心地追寻那个时代建造的教堂和管风琴的照片,一张一张收集起来。我还认识很多在教堂弹礼拜的人,他们弹到晚年。一个中国人在这种陌生的人和生活面前不仅暗自惊奇,心里往往装满忧伤,然后在忧伤中沉默。世上之不如意事也多,我天天忙得何止朝九晚五,而那来自管风琴世界的沙沙丝绸之声,让我觉得此生别无可恋。
忙中偷闲,要为这个人的音乐画些小像,让那声音边折射边穿越东方人竹林幽兰的绮思。就算是擦肩而过,到底有气场彼此叠加过吹拂过。
二、还是说说这个人吧
我们连他的出生记录都找不到,只有他的葬礼记录,说他享年多少岁,才推算出生年。不过我们总算知道这样的事实:老布是海边长大的孩子,一生离海不远。
当时的吕北克,社会等级森严。老布父亲是音乐家,但地位与引车卖浆者相平。这种人的出头之路,是找到最上层的贵族赞助人。老布继承父业,也要小心握牢一角关系网。当时,他有七个孩子,统统找了贵族做教父教母。他的音乐活动包括给贵族们写些小品。
当然,正经活动是教堂主日的演唱、演奏和作曲。跟巴赫一样,布克斯特胡德也是老牌的路德会教徒,而且当时吕北克路德会是绝对主流,老布的音乐地位跟教堂地位互相加强。当时的吕北克处于文化和商业低迷时期,有人将之归罪于路德会的大一统,也许有些道理。既然力主简朴、节欲,社会生活单调萧条也是必然后果。
当时吕北克有一些小教派,比如路德会内部分离出去的虔诚会,终归敌不过路德会,所以自己的音乐也就没那么影响深远。天才的老布碰巧跟对了风,不然我们可能听不到他了。不过,老布埋头为当时的教堂活动而写,好像并没打算或者企图流芳百世。他的一招一式,都老老实实地有着服务的目的。相比较而言,巴赫确实写了不少非教堂功能性的探索之作。这都是后话了。
P46-48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