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有关青春迷惘的小说。其中糅合了爱情和恐怖,情爱和自杀,以及回忆和想象。同名电影在美国上演,由著名新人影星克里斯滕·丹斯特担纲主演。
作者把我们引到美国七十年代的郊区,一座四周环线着榆树的房子里。李斯本夫妇一共养了五个漂亮女儿:有头脑的特丽萨、挑剔的玛丽、虔诚的邦妮、放荡的露卡丝以及纯洁而脆弱不禁风的塞西莉亚。但这五姐妹却神秘地接连自杀。小说通过一群邻家男孩的眼睛,开篇就写了玛丽服安眠药而死,继而又回顾了塞西莉亚的割腕自杀。
故事在倒叙中开始。这五个姐妹的言行情状,男孩们的困惑,神秘的青春以及青春时期的信仰,还有隐隐约约的忧愁恋爱。五姐妹性格迥然不同,有时却象是同一个人,男孩们总是通过扇窗口向对面观看着、迷恋着、迷惑着……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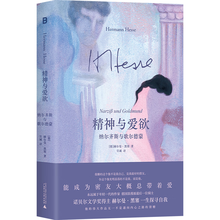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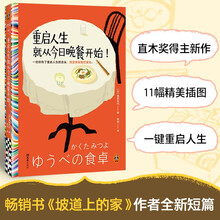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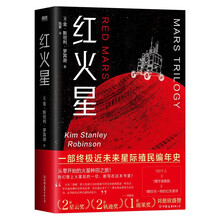

死亡,不需要理由
正像哈姆雷特那句脍炙人口的台词所言:“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生命的毁灭总给人以惊心动魄的震撼;尤其是在人们将上帝的特权夺过来,用自己的手结束生命之际,它更难以让人平静地正视。无怪乎法国作家加缪在《西西弗神话》开篇便将这一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从标题上便可得知,《处女自杀》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讲述的是花季少女自杀的故事。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李斯本家的五姐妹先后投入了死神的怀抱。很多时候,自杀有着明确的理由:接踵而至的打击使人脆弱的神经訇然崩塌,连绵不绝的不幸将生的乐趣消耗殆尽。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掐断生命导索的勇气。在各种各样的疑虑的牵制下,生命大多延续了下来。然而,这部小说中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李斯本家姑娘的自杀并没有具体可触的理由。第一个实施自杀,午仅13岁、排行最小的塞西莉亚就是这样。这个姑娘的自杀震动了整个街区,使她的全家陷入一种无法修补的残损状态之中。更重要的是,她为姐姐们树立了一个可资仿效妁楷模,像古希腊神话中塞壬的歌声,有着一种无法摆脱的魔力,它在那座房子里悄悄地蔓延,膨胀,一年之间竞使她的四个姐姐随她而去。
要知道,李斯本家的姑娘们不是生活在贫瘠的阿富汗,而是被人们目为天堂的美国。尽管她们的家境称不上富裕,但足于维持一种相对体面的生活方式,而这正是广大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度中的孩子们苦苦企盼的。可她们并不珍视这一切——作这种比较只有对局外人才有意义;对生活在这个沉闷的城市中的姑娘而言,她们根本体会不到这种巨大的反差。于是,她们中了邪魔般的自杀行为在美国这一天堂的背景上戳了一个硕大的窟窿,那令人心悸的黑洞将人们从沉滞的日常生活中唤醒,打扰着他们的美梦。曾几何时,冷战刚一结束,就有人迫不及待地站出来宣称历史已经终结。但就这一自杀事件而言,历史并没有终结。终结的是某些形式,但历史还是在前行。
还是回到李斯本家姑娘们身上,人们急切想要知道的是:她们为什么要自杀?这一巨大的问号沉甸甸地压在人们的心头,盘桓在人们的脑海中,尤其是那些钟爱她们的男孩,更想寻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小说的叙述便从那群男孩的视角展开,男孩们与李斯本家姑娘短暂的交往以及对她们命运的关注、惊诧、追寻成了整部小说的主要内容。在刨根问底的追寻中,总能找到某些线索,尽管可信度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霍尔尼克大夫是这样推断的,“自杀就像玩俄罗斯转盘……一颗子弹来自家长滥用职权;一颗子弹来自遗传基因的安排;一颗子弹来自历史的不爽;一颗子弹来自不可避免的动力”。这些都是理由,但似乎都打了擦边球,没有击中要害。
从那些男孩的目光来看,李斯本家的姑娘无疑分外强烈地感到了青春期的狂躁不安。但问题是这一切并没有到置人于死地的地步。尽管她们的母亲想要把她们软禁在家中(一度也的确这样做了),但她们并不是别无选择。她们有的是机会;只要她们愿意,她们完全可以远走高飞,摆脱那令人厌烦的环境。自然,未来并没有镀上玫瑰色的光焰,但它向她们还是敞开着大门。但她们不愿意。她们太累了,累到失去做任何新的尝试的地步。就在那些男孩想将她们带走之际,她们急不可耐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