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我已经在享受一个小小的发现了,那就是面包。面包又松又脆,并且有一点点耐嚼,我还从面前的白脱盘上取了一点淡淡的、将近白色的黄油涂在面包上。那个时候在英国,黄油还是咸咸的,蜡黄色的那种,拿出来的时候也是非常吝啬的一小块。第一口咬在法国面包和法国黄油上,我那还在沉睡中的味蕾突然苏醒了,一阵痉挛。
我想应该是一条高贵而威严的海鲈鱼,被隆重地端上了餐桌。侍者飞快地用勺和叉子把鱼分成薄片,小心地铺排在我的盘子里。我先前所经历过的鱼只有鳕鱼和欧蝶两种,而且是经过伪装、按照英国传统躲在一大堆厚厚的奶蛋糊之下的那种,与此相比,这条海鲈鱼就又白又香,看起来是那么古怪地裸露着身体。后来我才知道那香味是茴香的味道。一切都显得有些异乎寻常。
就连薯条也和英国那种结实的老土豆不同。这里的薯条是放在一个单独的盘子里。堆成金字塔的薯条每他“有铅笔那么粗细,咬下去脆脆的,嚼起来嫩嫩的,就着鲜美的鱼肉吃起来真是再好不过了。更幸运的是我不需要参加上级们的谈话;这样我就忙着去发现真正的食品。
然后就是奶酪。有几十种,甚至更多,在很多年里只有切达干酪和戈尔根朱勒干酪这两种选择之后,这又成了一个让我困惑的源泉。我看中了一块样子和切达干酪颇为类似的,指了指。侍者坚持给了我额外的两种,这样我就可以比较三种不同质地,从硬的,到适中的,到奶油般柔软的奶酪所带来的不同口感。味蕾上传来了更多的愉悦,像是在弥补我那么多年来失去的时光。
Tarte aux pommnes。连我都知道那是什么;杰金斯也知道。“好极了,”他说。“苹果派,只是不知道他们用的奶油对不对。”完全不同干我小时候吃惯了的、底上和顶上都有厚厚
一层皮的那种,眼前我的碟子上的苹果派赤裸着上身,露出水果——也就是切成一小片一小片的苹果,漂亮地交叠着,摆了好多层,在薄薄地一片奶酥般的糕点皮上闪烁着晶莹的光泽。
以我那时的年龄,还不配享受餐后昂贵的雪茄和白兰地,所以,我带着充实的胃坐着,有些晕眩,而我的同伴们则吞云吐雾,重新开始考虑办公事务。进餐的时候,我被允许喝了两杯葡萄酒。此时的我,已经有些微醺了,完全不记得我对杰金斯先生那个无比重要的公文包所担负的职责。离开餐馆的时候,我把它忘在了桌子底下,向他证明了我不是块做生意的料,这就是我在这家公司的职业生涯走向终结的开始。但重要的是,这顿午饭成了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失去了我的童贞,那种对美食一无所知的童贞,
不单是因为吃的东西,尽管那比起我以前所吃过的任何东西都不知要好上多少倍。更重要的是那种经历:典雅的餐桌摆设,开酒和品酒的礼仪,侍者们毫不唐突,却快速有效细致入微的服务。他们总是将盘子摆得恰到好处,适时地从桌布上将面包屑拂去。对我来说,那是一个特殊的场合。我不能想象人们每天这样吃饭,但在法国,他们就是这样。这就是我长期以来着迷于法国人和法国美食的缘起。
历史上,法国人就一直非常——有些人说是过分——重视吃饭和如何吃饭,当然这是最老套的说法,但陈词滥调通常是有一些事实根据的,这个说法大抵也是如此。法国人把钱都花在他们那张嘴上了,比起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居民,他们花费在食品和饮料上的钱占收入的比例是最高的。不仅是有钱的小资阶层将食物视为兴趣所在,从食物中获取享受和知识,从总统到老农的各个社会阶层都概莫能免。
学习吃——学习怎么吃——是一个充满了冒险和惊奇的过程。比方说,就在你以为你已经充分了解了土豆——这个最基本的、没有什么新意的食物的时候,你发现了阿里戈,那是将土豆泥、大蒜和康塔勒干酪拌在一起弄成的,口感像天鹅绒般柔滑。或者你又遇上了将小小的野草莓不是拌上奶油,而是拌着醋沙司”这种常人不太可能想到但又确实美味无比的吃法。然后,你又吃到了烤无花果。对胃的教育真是永无止境啊。
通常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愉快的过程。那些将生命致力于弄出美酒佳肴的人,总的来说是一群性格温和、易于相处的人,如果你对他们的劳动成果表现出一点兴趣,他们就会非常开心,并热心地向你介绍他们是怎么弄出这些美味的。我曾经见过一些在连续工作十四小时之后疲惫不堪、态度粗暴的厨子,我还记得见过凶个厨个,醉得从厨房门里倒出来,嘴里还在骂骂咧咧。但这只是特例。总的来说,和好吃的,好喝的打交道好像容易引出人性善的一面,很难想象一个悲观厌世的人会愿意花上许多时间,捣腾出能给他人带来满心愉悦的东西。
快乐是会传染的,这情形在每星期的有一顿饭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吃这顿的时候,你会看到孩子,父母,祖父母,有时候还包括家里的狗,聚居一堂,年轻的夫妇在犒劳自己;年长出老妇人和老绅士们在仔细阅读菜单,好像要从中找出人生的秘密;来自附近的家庭,个个穿上了最好的衣服,而远道而来的巴黎人则换上了具有乡土气息又不失时髦的装束——不同年龄,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汇拢到一处,全是因为另一个在法国不见有丝毫衰败的传统:星期日午餐。
对我而言,接下来的那些时刻和进餐本身一样让人受用:开胃酒已经斟满——茴香酒,干白葡萄酒、葡萄酒,或是在节假日的时候开的香槟酒——带着律师阅读法律文本的那股子专注劲,菜单也已经仔细阅读过。点什么菜,不点什么菜的讨论也跨越餐桌进行了好几个回合。是点新鲜的白汁三文鱼呢,还是罗勒大蒜浓汤?或是芦笋鸡蛋烘饼?然后呢?是香草饼包鳕鱼?辣椒炖小牛肉?还是小牛蹄与填牛肚,或是用普罗旺斯地区独有的方法烧成的,绝顶美味的羊肚?
实际上,点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焦灼等待的时刻。有那么五到十分钟,谈话安静下来,闲聊和家庭琐事被搁置在一边,餐馆中的每个人都在脑子里品尝着将要端上的菜肴。你几乎可以听列味蕾舒展开来的声音。
午餐的过程拌然有序,不慌不忙,其实任何像模像样的午餐都该那样。人们在星期日吃得就更慢了,喝得也要比平常多些。他们已经不记得要去看他们的手表。两小时,常常更多的时间过去了。最终,酒饱饭足,一股懒洋洋的镇定的气息缭绕在房里,盘子撇下,餐布打扫干净,咖啡端了上来。一个懒洋洋的下午就在眼前。看奉书,打个盹,游个泳。厨子庆功似地到餐桌旁巡视,按受称赞,然后高兴地传授最爱欢迎的那一两道菜的烹饪方法。奇怪的是,无论你如何严格地按照菜谱上的方法,也无沦烧荣的入钉天大的本事,这些菜如果是在家里烧出来的,味道总有些不一样。法国乡间餐厅中的星期天午餐里所包禽的,不单单是食品,还有那种氛
围。可惜的是,氛围是不会旅行的。
在准备此书——那些长时间地和刀、叉、酒杯打交道的时间,也就是我所说的研究过程中—— 我始终对两点感到特别好奇,第一是法国人那种将任何活动,无论是多么奇怪的活动,变成吃和喝的庆祝的热情。组织者、经营者,或是普通大众(在某些情况下,某些人穿越了大半个法国就是为了吃上一顿)所花费的气力让人瞳目结舌。我不能想象其他任何民族为了蛙腿、蜗牛,或是为了一只鸡的好坏而花上整个周末的时间。
第二个让我感到惊奇的地方在于,虽然法国人对美食的爱好是如此严肃,他们到了该享受这些美味的时候,自己却一点也不严肃。他们穿着奇怪的衣服,唱着最古怪的歌曲——比方说《到蒂帕雷里的路好长》之类——唱的时候扯着嗓门,还经常走调。他们互相取笑,吃吃喝喝,好像刚拿了一个冠军,把自己彻底放松下来——根本不像法国人惯有的名声:拘谨而冷淡。
礼堂里的人们愉快而吵闹,每个人都在桌边走来走去,查看桌上写着名字的纸片,寻找预定好的位子。我找到了我的,在寒暄声中和附近每一只能够得到的手握了一遍。他们都是些当地人,心情很好,嘴巴很干。
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作为一个外国人很划算。人人向你敬酒。还不单单是酒,他们还给你各式各样的忠告——无论你想不想听——因为他们认定你受教育的程度不够,许多事情只有法国人才能完全理解,所以你需要一点帮助。
就拿松露,也就是别称为“神圣的块菌。这样东西来打个比方。英国人根本不懂享受这珍馐美味,我这个从英国来的人怎么可能懂得松露是不能人工栽培的呢?它想长哪儿便长哪儿,任何人工培植都拿它没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每年的产量和价钱会相差如此之大。我的老师隔着桌子摇头晃脑,好像他自己参与制定了这条大自然规律一般。
我问他对当时新闻里常常出现的转基因食品有何看法时,他立马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可能是侮辱了他的祖母,或者更糟,漫骂了他喜欢的足球队。他指出,和大自然耍花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只不过是个为了让农民每年都得买新的种子、阻碍自然再生的阴谋位俩。一个丑闻,制造丑闻的是那些穿着白大褂从来不把他们的手弄脏的农业强盗,如果不是停下来喝酒的话,他看起来可以这样骂上好几小时呢。
煎蛋饼到来的时候,他终于彻底安静了下来,这是一份冒着热气、散发着芳香、洒上了许多黑松露碎片的煎蛋饼。蛋的颜色是鲜亮的明黄色,这种黄只有农场里自由放养的鸡下的蛋才会有,并且厨子精确掌握了烹饪的时间,使蛋微微流着黄,恰如其分地介于软和硬之间。用技术术语来说,这就是“流黄”(这个字法语的发音baveuse听起来可比直白的翻译诱人多了),这种状态和质感的鸡蛋是我多年来久觅而未得的。
我做的煎蛋饼,无论我的脑袋如何热切地在它们上空盘旋,它们最多也就比炒鸡蛋稍微强些。它们甚至不能被搬动,通常在从锅子到盘子这样短暂的行程中也会破裂开来。我从来就做不出那种丰润、柔软,金黄,可以从平底锅里干干净净地滑出来的蛋皮,我问我的邻座有什么秘诀。怎样才能做出完美的煎蛋饼?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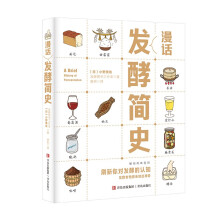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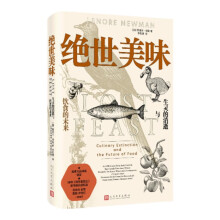




沈宏非
French Lessons直译为“法语课”。第一联想,是法国小说家都德(Daudet)的《最后一课》。小说里的那堂法语课之所以惊心动魄地好看,在于其无处不在的张力,也就是说,自始至终都笼罩着一个“禁止法语课”的巨大的阴影。大家都知道,这个阴影,这个敌人,指的是“只许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州教法语”的普鲁士当局,“那些坏家伙”。
拔剑四顾茫然的侠客说:“无敌最是寂寞。”“没有冲突,就没有故事,”这是小说家言。最起码,在叙事的技术层面,上法语课和吃喝活动一样,必须设置一个敌人,方能将口腔活动激活至空前活跃并刻骨铭心之境地。我们看到,一旦有旁的儿童在一起争抢,平时不肯好好吃饭的儿童通常都会因这些“普鲁士当局’的出现而突然变得胃口大开,甚至暴饮暴食起来。 梅尔先生深谙此道。在“普罗旺斯系列”中,那个英国人代表着我们大多数人营营役役的生活状态,与普罗旺斯懒洋洋的阳光之下的那种“神仙过的日子”大战三百回合,最后全身松软地、幸福地败下阵来,煞是好看。在大众的想象里,英国人,英国成年男人,本来就是“拘谨”或“沉闷”的代名词。这还不算,梅尔先生不仅是英国人,而且几乎就是地球上郁闷生活的杰出代表。上阵之前,他在麦迪逊大道上服了十五年的“苦役”,狼奔犬突,惨不忍睹。饮食问题上,英国和美国更是出了名的乏“膳”可陈,尤其是前者,用法国人的话来说,“只求一饱,不死就可”的英国人杀猪是杀两次的:第一次是杀猪,第二次杀的是猪肉做成的菜(当然,炸鱼薯条、猪肉馅饼、羊肉薄荷果酱以及什么牛肾烘饼之类的“淡出鸟来”,今天已逐渐淡出伦敦之时髦饮食圈。伦敦和纽约、巴黎一样,皆以fusion为最in旗帜——为之鼓与呼的彼得·梅尔似乎功不可没)。
至于英国人对待吃喝的态度,在我们的“想象共同体”当中,更一向被视为全人类之“美食公敌”。我们一直相信,或者将信将疑地相信,对待食色,英国人或多或少都怀有某种来历不明的原罪感。据英国饮食杂志Good Food称:“随着近年英国人开始慢慢的讲究美味,以往给外界留下的那种刻板印象正在逐渐被打破。”这种“刻板印象”是:“过去的英国人曾经是最不讲究吃的民族,他们认为食物不过只是用来填饱肚子的材料而已。”这一次,彼得·梅尔为我们制造的这个“有趣的坏蛋”以及“开胃的敌人”,依然是过去的那个“英国人”。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垂涎三尺,在由“刀叉和瓶塞钻”组成之法兰西阵中进行“历险”,老鼠掉进米缸,猪八戒闯进了女儿国,自然是加倍地活色生香,张力十足。当英式的“罪恶感”与法式的“最饿感”陷入混战,百感交集,岂有冷场之理?Adventures with Knife,Fork and Corkscre,与刀叉和瓶塞钻共同历险——正是这本书的副题。虽然在广大读者的想象中,梅尔于饮食一道早已修成正果,但是他似乎是越活越“回去”了——至少在这本书里,他老人家一上来便以一个“童贞丧失者”的形象出场:“第一口咬在法国面包和法国黄油上,我那还在沉睡中的味蕾突然苏醒了,一阵痉挛……我失去了我的童贞,那种对美食一无所知的童贞。”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这叫“饱食终日,常怀赤子之心”。听这个怀着“饮食原罪感”的英国人将其“丧失童贞”之全过程娓娓道来……“一阵痉挛”紧接着“一阵痉挛”,这回真的搞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