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故事》是帕乌斯托夫斯基卫国战争之后主要成就所在,是一部自传体作品,然而这部巨著却并不试图构筑苏联作家关于19至20世纪之交俄国历史与文化的普遍理念,这是很让文学史家疑惑的:19至20世纪之交是俄罗斯历史上一段特别重要的时期,是诸多俄国知识分子的重要叙述对象。高尔基的《克里木·萨姆金的医生》,是关于这一时代最隐晦难懂的文本;阿列克塞·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以全知视点叙述这时期的历史变迁如何促使知识界分化,这是关于这一题材的文本中最遭非议的文本;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以史学家和故事讲述人的双重身份在叙述地域性的世纪变化中透视俄国历史变化,是所有文本中争论最多、写实性最强的;安德烈·别雷的史诗化散文《世纪之交》、《世纪之初》和《两次革命之间》(不久将由东方出版社推出),力求真实纪录俄国知识界精神变迁过程,是对这一时期俄国思想史和知识界的状况叙述得最细致的文本。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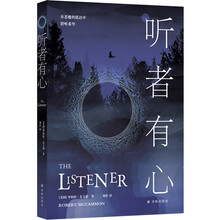






几 句 话
不久前我翻阅《托马斯·曼文集》,在他论作家劳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好像觉得,我们表达的只是我们自己,讲的只是我们自己的事,可是原来由于和周围人们的深刻联系,由于和周围的人具有本能的共同性,我们却创造了某种超越个人的东西……这种超越个人的东西,就是我们作品中所包含的最好的东西。”
真该把这几句话作为大多数自传性作品的题词。
作家表现自己,也就是表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这是一条简单的和不容置辩的规律。
这部作品包括六篇自传体小说:《遥远的岁月》、《动荡不安的青年时期》、《一个未知的时代的开始》、《怀着巨大希望的时期》、《投向南方》和《漫游的书》。同一主人公和同一时代把这些小说联结在一起。这些小说叙述的是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和本世纪最初几十年的事。
对于所有著作,特别是自传性质的作品,有一条神圣的规则——只有到作者能讲实话的时候才应写。
就其实质而言,每一位作家的创作,同时也就是他的自传,在某种程度上以想像力加以改变了的自传。这种情况几乎永远如此。
于是,写成了六部自传性的作品。我预见将来还会有几部这样的书,但能否写成,那就不知道了。
我想用一个早就使我不安的想法来结束这篇短短的引言。
除了一切符合事实的、我的真正的自传,我还想写一部可以称之为虚构的、我的第二部自传。在这部虚构的自传里,我愿在我经常幻想、但又是徒然幻想的那些令人惊奇的事件和人物当中描写自己的一生。
但不管将来我能写出什么作品,现在我却希望这六部小说的读者能体验到在过去的岁月里支配着我的那种感情——感觉到我们人类生存的重大意义和生活的深深的魅力。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