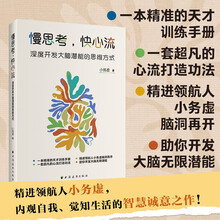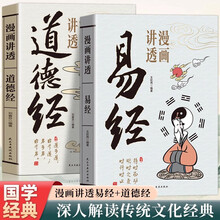她是作为“拉卜楞施教队”的一员进入甘青草原的,由于时间较短而且对该地区十分陌生,她只好采用了一种综合调查的方式。俞湘文在调查中往往缺乏前几位人类学家对调查对象的浪漫想象,而更多地看到了边疆之落后、闭塞、贫穷与}昆乱,所以她便总是带着教化与发展的眼光,呼吁对边疆的教育支持,并为当地的经济建设方向提出建议,甚至还提出了边疆政府机构改革的问题。她尤其重视的是边疆教育问题,希望从牧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到孩子的基本教育都进行一次科学的变革,但她显然并非一个文化同化主义者——在她看来,保留文化相对性和科学的普及原本就不是水火不容的。
陶云逵在去世之前已经是国内学界公认的知名人类学家。作为中国第一位“历史人类学”教授,陶云逵将此前半个世纪对德国学术的辗转学习落实成了扎实的民族志研究。“车里摆夷之生命环”是他为数不多的以具体民族和地方为对象的长篇民族志作品。所谓“生命环”本身就是一个时间概念,陶云逵发现,摆夷人的生命其实是在多个时间体系中往复循环的。尤其是小乘佛教的时间体系与巫官的时间体系既相互配合,又彼此排斥,而当地的宣慰史则要不停地跳跃于两种主要的时间体系之间,以完成对当地社会的整合。述评者杨清媚主要分析了陶云逵描述的年度周期仪式,不同仪式背后不同的宗教时间观念和宇宙哲学体系如何在当地交错共存构成了理解当地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一点推而广之对于理解中国文明的宇宙观体系的建构,以及政治一宗教格局都有很大启发。
被称为“南中宿学”的徐嘉瑞是云南史地专家,1944年受大理地方官绅所托开始著大理地方史,并于次年成稿,但因抗日烽火所迫,此书延至1949年才得以出版。与前述任乃强相近,这本《大理古代文化史》所寄托的徐氏心史,仍旧延续了地方知识分子对帝国的整体想象。如同述评者罗杨所指出的,它并非一部“乡邦”之史,而是以民族关系史的方式书写的文明史。徐嘉瑞借鉴了傅斯年、李济等人重建上古史的方式和考古发掘的成果,将大理文化源流的脉络直通史前。而对当时考古学还无法论证的夏朝甚至之前的历史,徐嘉瑞则从有关的史志中搜寻资料以佐证。在他看来,正是在从夏至西汉近两千年的“遂古期”第一阶段里,大理先后融合了夏文化、蜀文化和楚文化而成为一个华夏文明的储藏地带。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