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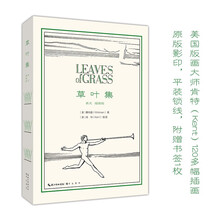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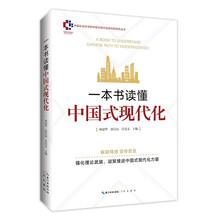


原文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 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语译
北方玄远的地方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鲲。鲲的巨大,不知有几千里。它蜕化而为鸟,名字叫作鹏。鹏的背脊,也不知有几千里。当它奋起而飞,它的翅膀好像天上垂下的一大片云。这只鸟,在海气运转的时候,就飞徙到南方玄远的地方。这里就是天池的所在。《齐谐》是一本记载怪异的书。该书上说:“鹏飞向南方玄远的地方的时候,首先水击有三千里那么长,接着再顺着扶摇的旋风向上直飞入九万里的高空,然后乘着六月的气息而去。”草泽中的水汽像野马奔腾,空气中的尘埃飞扬,以及各种生物以气息互相吹嘘。诸种景象都充塞在天地之间,我们向上看到一片蔚蓝的天空,难道这就是天的本色吗?还是因为距离太远、无穷无极?如果从高空向下看,情景也是一样的啊!如果水积得不够深厚,就没有力量负载大船。如果把一杯水倒在厅堂中的洼地里,只能以一根小草为船,浮在水面。如果把一只杯子当船,就会黏着在地上,这是因为水浅而船大。同理,风积得不够深厚的话,便没有力气载负巨大的翅膀。所以大鹏要直上九万里的高空,
使风积在下面,才能乘着它所造的风。脊背顶着青天,而不致坠落,然后它才向南而飞。这时,地面上的一只蝉和一只斑鸠讥笑鹏说:“我尽全力而飞,碰到榆枋等小树便停在上面。有时飞不到,最多再折返到地面。哪里需要直上九万里之后才向南飞呢?”如果是到近郊,只要带足三餐,回来后,肚子还不会饿。如果要到百里外的地方,就必须准备一夜的粮食。如果更远到千里之外的地方,一定要准备三个月的粮食,这两只小动物又哪会知道这个道理呢!小智慧不能了解大智慧的境界,寿命短的不能了解寿命长的经验。为什么如此?譬如见日即死的朝菌,不知道一个月的时光。只活在夏天的蟪蛄自然不知道春天和秋天,这就是所谓的小年。楚国的南部,有一只灵龟,以人间的五百岁为它的春,五百岁为它的秋。上古时候有一棵大树,以人间八百岁为它的春,八百岁为它的秋,这就是所谓的大年。今天我们以活了八百岁的彭祖为寿命最长的人,大家都想和他相比,岂不是很可悲?商汤问棘的那段话也是这样说的。在不毛之地的北方,有个广漠
无涯的大海,也就是天池,其中有一条鱼,身体宽有几千里,没有人知道它的长度,它的名字就叫作鲲。有一只鸟,名叫鹏。它的背脊像泰山那么高,它的翅膀像垂挂在天上的云,两翼拍着扶摇羊角的旋风而直上九万里的高空。冲破云气,背顶着青天,然后再往南,飞向南方遥远的地方。这时小泽中的麻雀讥笑大鹏说:“它究竟想飞到哪里去啊!我向上飞跃,不过几仞高,就降下来。我在蓬草之间飞来飞去,这也是我飞翔的最高境界。而它这样飞,又能飞到哪里呢?”这就是小大之间的不同啊!
解义
我们来看庄子是怎么写《逍遥游》的。他一开始就说“北冥有鱼”,那个场景是暗的,如《天下》篇中所说的“芴漠无形”,他说的是“北冥”不是“北溟”,如果是“溟”的话指的就是北海,但他说的不是北海,一说北海范围就小了,也落实了,他所说的“北冥”是无穷,看不清的北边,在那里有一条鱼叫作鲲。庄子笔锋一转就写到“鲲之大”,大是庄子思想的境界。但是鱼一定是由小到大的,这条鱼变成大鱼了,其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庄子用几千里来写大,还不是大,因为那只是一条鱼。时间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化而为鸟”,不是变为鸟,“变”与“化”两个字我们要区分开来,“变”就是由生到死,也就是形体的变化;“化”是转化,两个系统间的突破才是化,例如化蝶,是由毛毛虫突变为蝴蝶。在同一个系统之内的发展是变,比如我们说由生到死,在此期间我的肉体一直在变,这是一个系统内部的变化,等到死了以后化而为鸟,这就是化。变是一个生灭的现象,是一个平面的发展,化则是往上的发展,是两个系统的突破。所以由小鱼变成大鱼是“变”,由大鱼变成鸟是“化”。这个鸟叫鹏,庄子笔下的大鹏也是一个很大的形象,它“怒而飞”,这个“怒”也是努力的“努”,不是发脾气的“怒”,所以从这个“努”字就可以看出它内在的充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海运”就是海动,即气流之动,显现了气的变化。这种气流之动使得它能够往上冲,能够长距离飞行,从北冥飞到南冥。他又引证《齐谐》,说齐国有一本书也是专门讲鬼怪故事的,庄子的想法也是从当时的一些传说中提取出来的。“去以六月息者也”,鹏之飞要靠六月的气息,庄子生活在周代,用的是周历,跟我们农历所依据的夏历大概差了三个月,周代的六月大致是我们农历的三月。阳春三月,生机勃勃,所以在这样一个气流转变的节点上一飞冲天。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它飞得多高,“野马也,尘埃也”,就是指大鹏飞过后的灰尘像野马一样奔腾。接着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这两句话讲得很清楚了,水要足够深才能载得动大船,因为它的势要足够强,才能把船托得很高。鲲化为鹏是不简单的,因为不知道鱼经过多长时间才能变成大鲲,然后才能化为鹏。所以要积累势和气,不要以为它一下子就飞起来了,这需要长久的修养功夫才能飞,才能化。在大鹏飞到高空以后,地上有两只小麻雀在笑它,说大鹏飞得那么高才把翅膀展得开,太麻烦了,而自己想飞只要动一动翅膀,即使跳不到树上,掉下来也没有关系,反正离地很近。所以这两只小麻雀笑大鹏多此一举,似乎是说大鹏还不如自己逍遥自在。那到底谁更逍遥呢?这里面有一个对比,涉及庄子理想中的至人、真人的逍遥跟贩夫走卒的逍遥的对比,庄子的态度显而易见,他说:“之二虫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可见他认为两只小麻雀是小知,它们不知大鹏的境界,世俗小人不知至人、真人的境界,因为他们受到形体的拘束。郭象的《庄子注》非常有名,在这里他的注却认为小麻雀也逍遥,大鹏也逍遥,这两种逍遥是一样的。他故意忽略了后一句,因为他要拿庄子的东西作为他们浪漫的借口,魏晋的士人是很放任的,《列子》中记录了很多魏晋时期类似的思想,比如《杨朱篇》,就说圣人和凡夫俗子一样都是要死的,活一百年也是死,活二三十年也是死,横竖都是一死,那为什么要羡慕圣人呢?还不如酒色财气一把抓,且乐当前,反正都是一死嘛!我认为,“小大之辩”中的“大”有两种,一种是与小相对应的大,另一种是无穷的大。比如我现在很小,学了东西之后就会变大,然而这个大跟其他东西相比还是小,再学了一些后又变大了一点儿,但永远都是处于“小—大—小—大”的相对序列中。进行比较的小大都是现象界的,所以那个大不是真正的大,可能跟别的东西一比较就又变小了。真正意义上的大是无穷的大,就只有一个,没有其他的小可以与之相比。这也是《天下》篇要以天为宗的原因,那是无穷的高,无穷的开放,那才是真正的大,不是世俗中相对的小与大。我批评郭象和魏晋士人的注解,也就是要说明寓言都是借物体来比喻,物体或动物都拘于它们的形体,它们的变化不能超出形体的范围,也就是说,小麻雀再怎么有功夫,也无法突破形态大小的限制。如果小麻雀能够安于自身的逍遥,就麻雀来讲并没有错,但是人性不同,它是可以突破形体,向上提升的。如以物性来比喻人性,就会有一个错解,现在很多人解读《庄子》里很多寓言时出现的错误,就是被拘束在物性里面,不讲人性,人性是没有限制的,是可以向上发展的。人有两个面向,一个是物质的人、肉体的人,这部分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另一个是精神的人,是可以向上发展的,这是无限开放的。如果人也像动物一样,说自己没有办法选择,安于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把自己当作物一样的东西拘束在那里。所以要注意物性与人性之间的差距,我们可以说小麻雀和大鹏都是逍遥的,但是人不能把自己拘束于小麻雀的境界。用寓言来讲人性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产生误解,因为寓言常常用物性来比喻人性。但是古代人写文章,会很自然地拿物性来举例。比如孟子讲性善,他就用水往下流来比喻自然的性善,荀子则是用树木生长来比喻人性,这些都是片面的看法,不是真正的人性。所以这些都只是比喻。此外,我还有一种另类的思考:小草和大树相比较,小草会认为自己小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现在我们常常会把人为规定的大小之分放到小草和大树的比较中,不幸又转回来放到人的区别中,认为天生注定的有的人大,有的人小,所以我们要打破这种人为的分别。
导 读 / 1
内篇第一 逍遥游 / 11
内篇第二 齐物论 / 35
内篇第三 养生主 / 91
内篇第四 人间世 / 105
内篇第五 德充符 / 139
内篇第六 大宗师 / 161
内篇第七 应帝王 / 201
附 录 / 217
外篇·秋水:用文学技巧表达哲学思想的杰作 / 217
杂篇·天下:中国哲学史上第一篇对诸子各派思想的评论 / 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