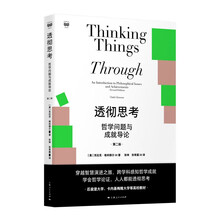四、作为后现代假说的泛经验论
相反,建设性的后现代哲学家们并不声称他们知道全部现实都有经验,但他们提出泛经验论是一种假说,即一种能使哲学家克服各种不足和用其他办法似乎显然不能解释的神秘事物的假说。这些显然不能解释的神秘事物之一,便是如何公平地对待我们在实践中都必然会预设的身与心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这种泛经验论的假说(它得到了我们五位作者的肯定),人们才能肯定这样两件使心灵与大脑之间的相互作用得以理解的事情:即心灵与大脑(在数量上)是不同的;但是心灵与大脑细胞(在本体论上)并不是不同类型的实体。
除了心一身关系的困惑之外,现代哲学家还有一个同样困难的、与自由和决定论问题密切相关的难题。它之所以密切相关,用皮尔士的话来说是因为:“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之间的区别乃是终极因与动力因之间的区别。”某些二元论的相互作用论者断言,自由不仅是人类心灵的自由,而且也是(通过心灵对其身体的影响)人类行为的自由。但是,认为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包括了自由与不自由的二元论只能增加心身相互作用的不可理解性。自由如何才能通过终极因或自决与不自由(它完全是由来自他物的动力因决定的)相互作用呢?中心状态的唯物论(无论它是采取一种同一论的形式,还是采取一种更为机能论的形式)通过否定人的自由,或者更典型地,通过重新定义它从而借助各种物理原因使之与彻底的决定论相一致,回避了这个问题。不可能有坎贝尔所谓的“形而上学选择”意义上的自由,这表明,选择不完全是由先前的物理原因决定的,因而部分地是自决的。坎贝尔指出:“如果有形而上学选择,那么中心状态的唯物论就是错误的。”而且同样,坎贝尔的附带现象论就会是正确的;更确切地说,他就可能通过心灵允许形而上学的选择,但又不可能允许这种选择影响身体的行为。然而,这种解决方式的问题是,每一个人(包括中心状态的唯物论者和附带现象论者)实际上都预设了我们要运用坎贝尔所谓的(或许有点贬抑意味的)“形而上学选择”——即包括了自决要素并因而是真正的自由在内的选择——而且,这些选择影响了我们的身体行为。既然如此,这就有一个矛盾,即一个在哲学理论的精确学说和哲学家实践的含混预设之间的矛盾。
避免说明经验和非经验、自由和被决定的相互作用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即当前最流行的方式之一——是,简单地‘否定心灵是自由的,而且,在事实上,它甚至作为一种现实而存在。心灵被认为是等同于(即在本体论上可以还原为)大脑的,而且,大脑的活动被认为是和任何其他自然活动一样完全是由动力因决定的。为这种立场而辩护的那种尝试已经导致了“消除式的唯物论”(eliminative materialism),即一种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学会不使用任何主观的语词(如“感觉”、“痛苦”和“目的”)就能完全描述人类行为的学说。其他一些认识到这种同一论方案是一个败笔的唯物论者则赞同机能论,它包含了这样一种主张,即我们所说的心灵(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大脑)完全是大脑的一种机能。尽管这是一种十分脆弱的、因而显然不太站得住脚的假说,但它仍否定了那些我们大家(包括提出这些假说的哲学家)实际上都预设了的观念——即我们的经验(包括制定和评价假说的活动)在现在部分地是自决的,而非完全是由先前的事件决定的。我们部分地是根据我们想要达到的理想目的作出自由选择的,而且,我们的目的即部分自决的经验影响了我们的身体,因而影响了世界。
唯物论解决心一身问题的途径阐明了另一种类型的反理性主义,怀特海发现,这种典型的现代哲学(除了那些安于满足矛盾的类型以外)“未能包括体系范围内的某些明显的经验要素,乃是和大胆地否认这些事实吻合的。”关于那些其体系排除了任何根据物理规律和化学规律都不能解释的事物的科学家,怀特海评论道:“他们构成了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这一论述同样完全适用于许多现代哲学家。怀特海指出:“拒斥任何证据的来源,总是对那种极力主张科学与哲学是相似的极端唯理论的反叛。”这种极端唯理论包括了这样一种适当而一致的倾向(drive):
宇宙论高于万物应该是恰当的。它不应将自己限定为一门科学的范畴概念,而应该说明一切不适应的东西。其职责不是拒斥经验,而是发现最一般的说明体系。在这一基础之上,他特别赞扬了他认识的一位哲学家(这位哲学家有时由于反理智而受到批评),他就是威廉·詹姆士:“他的理智生活就是反对为了体系而摈弃经验。”
基思·坎贝尔之所以拒斥唯物论而赞同附带现象论是因为,他认为唯物论的同一论和机能论不能公正地对待人类的经验。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附带现象论既是矛盾的(和其他形式的本体论二元论一样),也是不当的。
二元论、附带现象论和唯物论的这种矛盾和不当,可以通过建立在泛经验论基础上的建设性的后现代哲学家而避免。泛经验论认为,所有个体(包括非人类个体)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真正(自决)自由的个体,并认为,不同等级的个体具有不同程度的自由。用皮尔士的话来说:“所有现象都是一种特殊现象,尽管某些现象是更具精神性和自发性的现象,其他现象是更具物质性和规则性的现象。同样,所有现象仍表现为(一种)自由和强制的混和。”因此,心灵和大脑细胞的相互作用并不介乎自由与不自由之间,而是介乎自由的多与少之间。以下各篇论文(特别是关于怀特海和哈茨霍恩的那两篇论文)将给出进一步的说明。
他们的观点和他们之前的詹姆士的观点一样,乃是建立在柏格森的这样一种洞见基础之上的,即现代科学似乎已经使自由成为不可能的原因在于,它试图把绵延(duration)即我们的经验还原为现代物理学中“空间化了的”时间。柏格森揭示了这种“时间”成为一种抽象的方式,这种使绵延即我们的内在经验符合物理学的时间的方式,不是要从我们的思想体系中排除绵延,而是要认识物理学理论的时间的抽象性,因此可以说,物理学讨论的具体现实和我们一样享有绵延。
然而,这却给我们带来了现代哲学的另一个困难,即如何使我们关于时间的预设成为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大多数哲学家都接受了关于我们的宇宙的进化历史(story),根据这一历史,生命产生之前经过了数十亿年的时间。另一方面,大多数思考过时间本质的哲学家——如阿道夫·格鲁鲍姆(Adolf Griinbaum)——又认为,时间,在我们经验它的时候,具有一种在场的(present)“现在”(它区分了过去和未来)和一种不可逆的方向,它不可能脱离经验而存在。那些想把经验完全归结为人类存在的哲学家们显然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