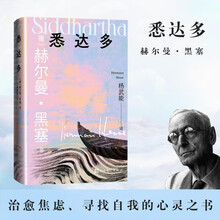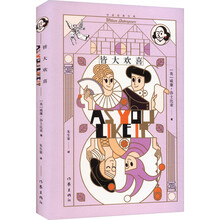《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
正如古典诗学所说的,读者从中间开始(in medias res),从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奥勃隆斯基(斯季瓦)的无关紧要然而令人痛心的不忠行为开始。托尔斯泰描述了奥勃隆斯基逢场作戏的私通行为,以不动声色的方式陈述了小说的主题。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向他的妹妹安娜·卡列尼娜求助。安娜正在赶往哥哥家的路上,希望恢复哥哥家里的平静。安娜以破裂婚姻修复者的身份出现,这是具有震撼效果的讽刺之笔,与莎士比亚所用的怜悯讽刺手法非常类似,两者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与愤慨不已的妻子多莉之间的交谈尽管不乏喜剧因素,却预示了安娜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之间的悲剧冲突。但是,奥勃隆斯基这一情节所起的作用超过了序曲,作品主题以极高的艺术手法陈述出来;它是一个轮子,让由许多部分组成的叙事之轮悄然运转。其原因在于,斯捷潘的家庭事务中形成的大破坏将会带来机会,让安娜邂逅伏伦斯基。
奥勃隆斯基到办公室——他得到这个位置,完全仰仗了自己难以对付的姻弟、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列文——去,在那里和列文汇合。列文“身强体壮,用一只手可以举起182磅重的东西”。他带着特有的情绪走进办公室。他透露说,他自己已经不再参加县议会的活动了。他取笑说,奥勃隆斯基获得的这个职位薪俸不菲,然而却几乎无事可干,认为它象征着呆板的官僚制度。然后,他承认,他到莫斯科来的原因是他爱上了奥勃隆斯基的小姨妹吉娣·谢尔巴茨卡娅。列文初次露面,读者便推测到他生活中的主要冲动:追求农业经营和乡村改革,排斥城镇文化,充满激情地爱着吉娣。
在接着出现的几个事件中,列文的个性得以进一步明确。他见到了异父兄弟、著名的宣传者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打听到哥哥尼古拉的情况,接着恢复与吉娣的接触。这完全是一个托尔斯泰式的场景:“花园中的老白桦树枝蔓缠绕,覆盖着厚厚的白雪,看上去仿佛刚刚披上了神圣的祭袍。”吉娣和列文一起滑雪,两人沉浸在清新、明亮的光线之中。如果从严格的叙事简略性角度看,列文与科兹内舍夫的交谈应被视为离开主线的插入性长篇话题。但是,其原因在于,在托尔斯泰小说的结构之内,这样的插入起到了特殊作用——我在后面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列文与奥勃隆斯基会合,两人一起在德安格勒特热酒店用午餐。酒店富丽堂皇,让列文觉得不悦。鞑靼侍者端上精美可口的大餐,他说他更喜欢“白菜汤和麦片粥”。奥勃隆斯基看到午餐后兴高采烈,但是心里仍被苦恼所折磨,问列文对夫妻之间行为不忠持何看法。两人之间这一段对话是叙事文学中的杰作。列文完全不能理解这种情况:一个人吃饱喝足以后,“转身又到面包店里面去偷面包卷”。他的信念带有强烈的一夫一妻制特点,当奥勃隆斯基暗指《圣经》中提到的抹大拉的玛利亚时,列文痛苦地说,基督是不会说这番话的:“假如上帝知道他们将受到伤害……我厌恶堕落女子。”然而,在小说后面的情节中,没有哪个人以更具怜悯的理解态度来对待安娜。接着,列文求助于柏拉图的《会饮篇》(Symposion),说出了自己关于爱情唯一性的观点。然而,他突然停下了话头;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他做的事情与他的信念背道而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许多问题都集中在这些冲突上:一夫一妻制与性行为自由、个人理想与个人行为、最初从哲学角度解释经验的行为与后来以基督的形象来解释经验的行为。
接着,小说的场景转到吉娣的家里。读者见到了爱情四方舞中的第四个主角,伏伦斯基伯爵。他以吉娣的仰慕者和追求者的身份出现在小说中。这个例子不仅是托尔斯泰的精湛技巧的表现,也是作者反驳读者的习惯反应的手法,与他们在生活中受到反驳的情形非常类似。这是“现实主义”的一种表达方式,是伟大艺术具有的“深呼吸的简略性”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看到,伏伦斯基与吉娣调情;这种行为具有的结构价值和心理价值与罗密欧迷恋罗莎琳的做法如出一辙。其原因在于,罗密欧对朱丽叶的崇拜产生改变一切的效果,伏伦斯基对安娜的激情也有改变一切的效果。这一点只有通过诗意的形式才能实现,只有在与以前的爱情进行对比的状态下才变得合情合理。他们发现,这两种东西迥然不同,一种是以前的爱情经历,另一种是人成熟之后遭遇激情时引起的恶魔般的全身心投入。这一发现驱使双方堕入无理性状态,堕入灾难的深渊。同理,吉娣对伏伦斯基的幼稚迷恋(这类似于《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对博尔孔斯基的爱恋)也是自我认识的序曲。正是通过对比,她意识到了自己对列文的感情的真实性。伏伦斯基给吉娣带来觉醒,这将使她放弃莫斯科的繁华,跟着列文回到庄园去。托尔斯泰以如此微妙然而又如此自然的方式,构成了故事的情节线索。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