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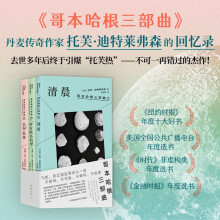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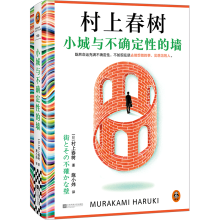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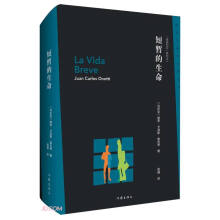







★ 一个女人。一位母亲。一个常常失眠的人。一个离婚后独居,但坚持称前夫为“我丈夫”的人。一个受挫的恋人。一个用索引卡整理自己生活的人……我和你,过去、现在和将来,无法逃离又无法抗拒。
★ 每一个从小地方来到大都市的人们都能从莉迪亚·戴维斯的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孤独、游离和不安,尤其是书中人的爱情故事、生存境遇,会让你有强烈的感受——碎片化的现实,比完整的故事更有趣。
★ 法式、极简结构,还有哲学家的冷酷等等,都让莉迪亚·戴维斯的作品在文学圈中显得卓尔不群。美国文学中独树一帜的作品,它们清晰明了,格言般简洁,形式独特,狡黠的幽默,抽象的苍白,哲学思考带来的压迫感,还有人类的智慧。
★ 莉迪亚·戴维斯的小说已然成为美国文学中一种伟大而又独特的声音,这些故事如此与众不同,带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好像弗兰纳里·奥康纳、唐纳德·巴塞尔姆的作品一样耀眼。
★ 可以说,自我中心这个词所囊括的一切,就是莉迪亚·戴维斯的真正主题:自我的蛮横的存在;自我的持续不断的内在声音;像讨债人一样躲不过的那个你究竟是谁的自我。
★ 我们可以从莉迪亚·戴维斯的幽默谈起。她以冷峻著称(很奇怪,有些人说她“阴沉”),但她的语调却是像跳舞般的、无忧无虑的,而且常常很好玩。有时,她最短小的那些作品是最甜蜜的心理游戏,就像某些现代艺术装置的说明一样(就是那种难得一见的既迷人又不让人发疯的稀有货)。
★ 85篇各具特性的小说,给人以全新感受,且极富冲击力,形式灵活。
★ 戴维斯是保罗·奥斯特的前妻,典型的文艺情侣,迥然两异的文风。
★ 设计师陆智昌倾情设计。
本书是2013年布克国际奖得主、美国女作家莉迪亚·戴维斯的获奖作品,包含《莉迪亚•戴维斯小说集》(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Lydia Davis,2009)的前两部分,即《拆开来算》(Break It Down,1986)与《几乎没有记忆》(Almost No Memory,1997)。
操劳的母亲研读《圣经》;陷入困境的分析师在结束治疗回家的路上,试图用一篇艰涩的法语文章来分散注意力;曾经的钢琴家试图证明自己对某个电视节目的依赖是合理的……本书以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视角,生动展现了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深层情感和复杂心理,揭露了当代人面临的普遍精神困境,诙谐而又克制,饱含着智慧与哲思。
【金句选摘】
1.想要入睡总是很难。即使有些晚上最后发现也没有那么难,但因为她预期会很难并做了这种准备,所以可能还不如说它很难。
2.她感觉不到任何一天的结束。每一件事情都在继续。事情不仅没有结束,可能也没有做得足够好。
3.这个夜晚很宁静,光线顺滑而柔软,土地沉睡着,在遥远的地面上,我,是那唯一移动的生物。
4.只有在说一些无聊的事情时我才能说很长时间。
5.突然他被房间里的寂静惊醒了。
6.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为家庭的奇怪性质感到迷惑了——家庭常常将那些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的人绑在一起。
7.当我一个人住的时候我拥有我所需要的一切宁静。
8.在明亮、尖锐的阳光下,橄榄树的阴影就像一条暗河一般流过石子,又拍上墙壁。
【文摘】
雪松树
当我们的女人全部变成雪松树时,她们会围在墓园的一角,在大风里哀吟。妻子刚走时,我们的精神很振奋,我们都认为那声音很美。然后我们不再注意那声音了,我们开始变得不安,彼此之间经常吵架。
那一年经常刮大风。我们的村子陷入前所未有的骚动。燕子飞不起来,而是东飞西撞,然后沉落到安静的角落里;瓦片从屋顶上剥落,碎裂在人行道上。灌木丛抽打着我们低矮的窗户。一夜又一夜,我们疯狂纵饮,在彼此怀里入睡。
春天到来时,风平息了下去,阳光很强烈。夜晚,长长的影子拖过我们的地板,只有刀刃的闪光才不会被黑暗吞没。那黑暗也笼罩着我们的心绪。我们对彼此不再有善意的语言。我们不情不愿地去地里干活。我们沉默不语地看着来看我们的喷泉和教堂的陌生人:我们靠在喷泉的出水处,穿着靴子的腿交叉着,我们残废的狗躲避着我们。
然后道路开始失修。不再有陌生人来了。连旅行布道的牧师都不敢走进我们的村子了,尽管阳光闪耀在喷泉的水面上,底下山谷里的果树和坚果树上开满了白花,灼热的阳光在正午时分渗进教堂粉色的石头里,黄昏时又退散开去。猫在被压实的地面上踱来踱去,从一个门口走到另一个门口。鸟儿在我们身后的树林里鸣唱。我们无望地等待着有人来访,饥饿啃噬着我们的胃。
终于,在那些雪松树心底深处的某个地方,我们的妻子被扰动了,想起了我们。在我们看来,她们慵懒地,无甚所谓地,回到了家。看着她们尖刻的嘴唇,冷硬的眼神,我们的心融化了。在她们刺耳的说话声中,我们就像刚从沙漠里出来的男人一样纵酒狂欢。
…………
译后记
戴维斯的“个性”
一个女人,一名英语教授,一位作家,一位法语文学译者,一位母亲,一个常常失眠的人,一个离婚后独居但坚持称前夫为“我丈夫”的人,一个受挫的恋人,一个用索引卡整理自己生活的人……这些,是莉迪亚 · 戴维斯数量庞大的短篇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形象。她们或许是同一个人,或许不是—我们无从判断,毕竟,对于戴维斯的人物,我们所知甚少。她们没有名字,来历不详。我们不知道她们的年龄、身高、长相。我们不知道她们在哪里出生,在哪里上过学,童年或青春期的创伤经验(这是多数现代小说家极力挖掘的),有过几段恋情。我们拥有的只是一个人称代词,一个“她”,这个“她”时而会被称作“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被放置于一个几乎像是不存在的地点—一个无名的小镇,一个无名的村子,一个无名的城市。仅在极为必要的时候我们才被告知,在某个故事中我们被暂时性地转移到了某个(依然是无名的)法国乡村。在这些故事中,读者很难辨认出传统小说的重要元素—情节不再清晰,叙事线索不再完整,冲突不再由精心搭建的场景来呈现,甚至不再有对话(而是由一个孤独的叙事者报告另一个人对她说的话)。它们能被称为小说吗?或者,将它们称作散文更合适?或是内心独白?或是场景速写?
在另外一些故事中,我们则被带到了一些奇怪的领地。这些故事往往都很短,不超过一页纸。在一个故事中,女人们都变成了雪松树,她们围绕在墓地旁,在大风中哀吟,“男人们则疯狂纵饮,在彼此怀里入睡”;或者,一间屋子里住着一个悄无声息的妹夫,是谁的妹夫无人知晓,而他付的钱会变成“祖母的大盘子上一团银绿色的雾”;又或者,在“我们的镇上”,一个男人既是一条狗又是它的主人,主人对狗极不公正,“头一分钟他想和它玩,下一分钟他又会因为它太难管而狠狠打它,让它屈服”,而在某些感到孤独的夜晚他又会把狗拉到身边来睡,“尽管那狗会因为恐惧而发抖”。很显然,这些故事又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它们是寓言吗?或许是(就像科塔萨尔的《动物寓言集》中的那些)。它们是童话吗?也可以算(我们既认出了卡尔维诺,又读出了安吉拉 · 卡特)。很显然,它们不想成为“故事”,也十分自觉地不以故事自诩。在这些简洁、紧凑、突然而怪异的“断片”(让我们姑且这样称呼它们)中,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作者的机智与自信,以及一种灵动而趣味十足的想象力。
初次读到戴维斯小说的人无疑都会受到巨大冲击—毫无疑问,它们与我们读惯的契诃夫式的短篇小说相去甚远。它们形式上是那样的新颖与怪异,那样的不合常规,那样的灵活与多样,而有时候,又显得那样的任性与一意孤行。而当我们打开《莉迪亚·戴维斯小说集》(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Lydia Davis)随意读过一阵之后(不需遵循任何顺序,随意跳读便好),我们又发现了一种令人惊异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难以解释,也难以被命名。但却像许多美国作家(例如弗朗辛 · 普罗斯[Francine Prose]、本 · 马库斯[Ben Marcus])所观察到的那样,戴维斯的作品绝不会与其他人的作品相混淆 ;进一步说,一个戴维斯的故事,即便拿掉作者的名字,你依然能立刻认出它是戴维斯的作品。这种效果是惊人的—有多少作家敢于宣称自己的作品在不署名时也能被读者辨认出来呢?或许,这种极具辨识度的东西就是评论家口中的风格。但我认为戴维斯的独特是某种比风格更尖锐、更偏执也更内在化的东西,我倒是愿意方便地将其称为“个性”。
…………
吴永熹
2014 年 8 月于纽约
(选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