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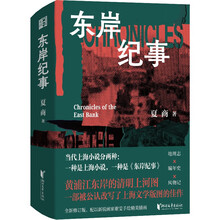




15. ◆正文赏读◆
老阎回到工程队队部,坐立不安。他看了这乱七八糟的办公室,就想发火。吃冤枉的通信员,眼睁睁地走进走出,也懒得把办公室收拾一下。他讨厌那桌上堆积的文件;讨厌墙上那颜色灰暗的平面图;黑色的电话机看来更不顺眼:平时,它不停地叫着,送来让人非常兴奋的消息,送来让人忧心如焚的情况,目下,它却死一般地冰冷和沉默。老阎心里千头万绪,任凭怎样使劲,也理不出头绪。其实,并不复杂,那不过是一种无限后悔的心情煎熬他:为什么让小刘过江去呢?我应该过江去,即使事后有人指责说“你放弃了领导责任,你必须对严重的后果负责”,也甘心情愿!
这工夫,办公室周围挤满了职工、妇女和小孩,其中也有韦珍。大家披风淋雨,等待着,等待着,等待小刘的消息,等待亲人的音信,等待决定命运的时刻。
在这些等待消息的人当中,只有韦珍显得特别。她一会儿走到队部门前,一会儿走到大树底下,一会儿又急急地走到某一个妇女跟前。她为什么走来走去,连她自己也弄不清楚。她的眼睛仿佛在询问天,询问地,询问面前所有的人:“工地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她的眼珠子虽然转来转去,但是并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从未经历过的严重打击和惊慌的心情,搅得她头昏眼花!
突然,队部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
这声音,使围在房子周围的人,骤然获得了生气,接着就欢呼起来了。大家奔走相告……只有韦珍仿佛没有听到什么似的。她靠墙站在那里,抱着安全帽,生怕它飞掉似的,翻起眼仰望天空,任凭雨水顺鼻子两边流下来,流过脖子,流进衬衣领子里头。她一动也不动,仿佛不思不想,其实,她在想着一件事情,或者说,一个记忆中的印象,那么固执地占据了她的脑子。这就是她刚来到这第九工程队,头一回看见小刘的印象。那时光,虎头虎脑的小刘,正抡起胳膊,脸红脖子粗地和一位同志争论问题,韦珍并不同意小刘的说法,因为刚来这里工作,不好表示什么,可是心里很不舒坦。这一阵子,那不愉快的印象,变得这么生动,这么亲切;小刘和别人争论问题时急躁的样子,满头茅草堆一样的硬头发,明亮而激动的眼睛,都是这样清楚地出现在眼前。不知道哪个家属拉了韦珍一把,她才像苏醒过来似的,弄清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一阵震动通过心头。这震动给她带来滚热的眼泪。她连忙用手帕擦了擦眼睛,抹抹鬓角的雨水,向队部办公室门口跑去,途中,有好几次慌慌张张碰到家属身上。
电话铃的响声,一下子使办公室变得明亮而充满生气。这声音,把大江那面的工地上一万多工人的心跟这指挥机关联系起来了。
老阎也像一下子年轻了十岁,红光满面,眼睛里喷射出欢乐的情绪。风雨呀,洪水呀,工期呀,梁建的情绪呀,这一切比起电话铃的响声来,都无关紧要。
老阎想扑过去,捞起耳机,用全身气力说几句话,可是生怕眼前的景象只是一场幻梦,于是犹豫着……这工夫,调度员机敏得像个猴子似的,两手一拍,嗖地坐到桌子上,抱住了电话机,弯下腰,两手捂住耳机送话的地方,喊:“哎呀!是你?当真是你?我的小爷爷呀!”调度员跳下来,把耳机递给阎队长,说:“小刘!当真是小刘!”然后,他站到那里,眨眼吐舌头,还不住地搔着后脑勺
。
老阎双手抓住耳机,问:“哦!你是小刘?我——阎兴。电话通了!哎哟,你这个小家伙!一过江就昏过去了?你的脚怎么样?肿啦?要小心。要千万小心。工地有卫生员。你仔细说说工人们的情绪怎么样?好,好!绝壁上吊着过去使用过的安全绳,利用它往上爬。派几十名工人,爬上绝壁,从森林里钻过去,到后山百十里的地方和县人民委员会联系,弄些粮食和熟食。要大伙停止工作。小刘!要关心同志们,人是无价宝。好!晚上通话。你可别拉住绳子上了山,去搞粮食。要听话。好,好!”他放下耳机,又想起了什么,连忙抓起耳机,问:“小刘?要小刘讲话。啊,小刘,你刚才讲话的时候,牙关子直响,是不是生病了?身上发烧?”
耳机里送来小刘的声音:“哪里!哪里!你只管放心。谁要看我表演,我还可以在钢丝绳上来回过几趟!”
老阎说:“调皮的小家伙!要注意身体啊!”
老阎放下耳机,又觉得:他刚才只是把那最先涌上脑子的话不连贯地说了几句,好像最重要的话还没有讲。他搓着手,耸着肩,噔噔噔地走过来,噔噔噔地走过去,眼睛总不离电话机。有时候,还侧着脸把耳朵贴近电话机,好像这个电话机会自动跟他交谈似的。小巧玲珑的电话机,叫人喜爱的电话机!嘿,难怪战士们把你从朝鲜战场千里迢迢地携带到这山沟里来!
老阎兴奋地在房子里走着,时而低声哼着快乐的曲调,用指头在桌子上敲着鼓点,时而朝外看,他希望有人走进办公室,随便聊点什么,哪怕是平时最不顺眼的人也好。对啦,洪水把老婆和孩子赶到哪里去了?也许雨水把他们喷得生病了!那个牙牙学语的小女儿多逗人爱啊!她要病了才够麻烦!千忙万忙,也一定要抽空去看看他们……
目录
在和平的日子里
一部有待重评的文学经典
——略谈杜鹏程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
吴义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