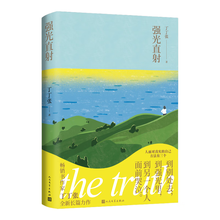蚁子回去叫大哥
那时没有电游,没有手机玩,也很少有人戴眼镜,只有那些做针线活的老奶奶和有点文墨的老爷爷看那线装的古书,才配有眼镜,或者是那些盲人戴眼镜,好扮,才有眼镜这东西。孩子们是不见有戴眼镜的。我们那时玩得很开心,整个暑假,帮家里割一些草或者干放牛的农活,大多数的时间玩得疯得起——去偷摘果木,去洗冷水澡,或者上下午浸泡在水里,脸上呈现死白色,家长也懒得管,当然也有意外的出现。我们还玩一些有趣的游戏。
整个夏秋天的闲暇时间,觉得特别短,好像没有现在这样难熬的苦夏,也不觉“24只秋老虎”这样燥热。我们总不会呆坐着,在厅堂里,或小巷中,四处是泥地,土砖墙下面的两三斗烟砖中,有很多小缝隙,在那弯弯曲曲的小通道中,是蚂蚁子民的家。它们簇簇拥拥,堆堆叠叠,从来不嫌陋室的狭窄,子子孙孙团团结结,和和睦睦,一如既往地以大家庭为荣,在暖和的春天开始的时候,它们整个家族亢奋不已,蚁后和雄蚁负责繁衍。工蚁将洞穴内的松垮的泥土搬运出来,日夜不歇,有些累死在劳作中,兄弟姐妹们哭一场,将尸体掩埋一下,又前仆后继地战斗。它们忧患意识非常强,它们温饱思饥饿,人却没它们那样明智,在空虚中只知道温饱思淫欲。它们在这高温的季节,又要为冬日里粮食的储备进行紧张地劳作。
日子在慢慢地晃悠,天气由暖和转成闷热、继而燥热,我们有时不想出去,于是我们在这时,突然对蚂蚁感起兴趣来,逗它们玩,以此来度过一些龟缩在阴凉处的夏季秋季的日子,从三岁开始玩起,玩到了不穿开裆裤,还在玩。我们拿起爷爷奶奶的大蒲扇,拍打着那些贪婪地啃着鸡鸭牛羊等粪便的大苍蝇或者是老实忠厚黄牛肚皮上的牛虻,我们只能拍打大个头的苍蝇,老虎是打不到的。奶奶这时,迈着蹒跚的脚步,追赶着我们:“小猴儿们,把我的扇搞腌脏了啊……”
“看!把我的扇拍烂了……”是的,这扇是他们纳凉的好工具。他们摇动着大蒲扇,迎暑送秋,看着天上流星的坠落,看着河汉从东西纵贯到慢慢横跨了南北走向,从显得朦胧的天河,逐渐变得高远清晰浩瀚无垠中呈现幽蓝中衬托的光带。萤火虫在孩子的手掌里忽闪忽闪的,如一个快乐的分子,游离在乡村遍野,营造成一个安逸祥和的世界……蒲扇是他们夏秋不离手的宝贝儿,他们如牛马一样,嘴巴微嗑个不停,不停地反刍着,但岁月似乎无痕。
但我们当时体验不到老人们那种敝帚自珍的感受,只觉得用扇能拍打苍蝇,苍蝇又是蚁们争抢的佳肴,当然还有蚯蚓,掉在地上的饭粒……
我们捏来一只那触角还在蠕动的小东西,寻找爬行在地坪上、厅庭里、小巷中的蚂蚁们,有意将诱饵放在它们前方的位置,有时,将苍蝇放在它们的面前,它们绕道而行,不理不睬,它们似乎为不辱使命,正在匆匆前行。我们重复几次动作后,看到它们不吃这一套,我们又另寻蚂蚁们。看,它停住了脚步,嘴唇的触须将地上的猎物勾动一下,一个蚂蚁搬不动,它就匆匆折转身搬援兵去了,于是,我们嘴里反复地哼唱着:“蚁子回去叫大哥……蚁子回去叫大哥……”
很快援兵到,晃动着脑袋去拖那猎物,一般它准确地估算了多少援兵的,一起抬起着那苍蝇的尸体就走。我们不能让它们那样容易获取猎物,要给它们制造一点儿障碍,将早已准备了的洗帚签(小竹签子),从那苍蝇的身体穿透,另一头,我们压上小石头,它们显然是移动不了,抬不起走动,只好又回去搬援兵,到头来还是挪不动,它们无法估量猎物的重量,它们又回去喊援兵,粗大,胖胖的蚁头也倾巢出动了,总还是要给它们一点希望,我们拿开小石头,让它们飞快地行动,又复石压起,之后又还是抬不动了。有时从压微小的沙粒,到小石子,我们总是层层加码,这样还不刺激,我们又用那穿着的蝇子,去引诱另一伙蚁群,引起它们发生争端,甚至你死我活地打起仗来,我们玩得津津有味,蚁们如诸侯纷争,军阀割据,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我们才觉得过瘾。
太阳像个大火球,炽热地挂在中天,爷爷从田间匆匆回来,下巴上的胡须挂着露珠似的汗水,一双浑浊的眼睛凶狠狠地瞪着我们这些小屁孩,叫得正欢的我们当然不畏怕他,他烦躁地取下头上的草帽,拼命地扇着风,似乎又跟谁赌气似的,咬牙切齿地看着天井上那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嘴里挤出几个字:“青石板……不下一点儿雨。”椅子上有堆鸡婆屙的屎,滑稽可笑如青螺一般,仿佛还冒着腾腾热气,爷爷似乎没有看见,屁股挨上去,在逗蚁们玩的小孩大声说:“凳上有鸡屎!”爷爷抬起了屁股,旋即又将屁股重重地墩上去,嘴里又大声说着:“挨死去,挨死去……怕你奶奶不洗衣服吗?”玩蚂蚁、叫回去叫大哥的游戏的小孩哈哈大笑不止,还两手拍起来,奶奶还不知怎么回事,嘴里骂着,“死老头,今天能下得雨吗,晒了豆荚子,晒了谷……”奶奶念叨个没完。小孩还是手指着爷爷,“鸡屎,爷爷屁股压着了……”
P3-4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