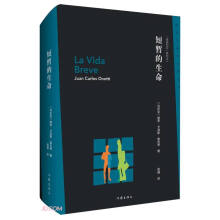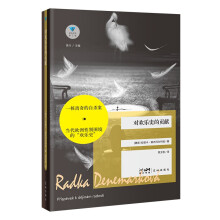《索尼娅的驾驶课(典藏版)》:
埃伦把温暖的双手放在索尼娅的上臂上。
“这太不公平了。”
索尼娅能感觉到自己右上臂的肌肉有所放松。是埃伦的手,它们在拍打她,埃伦的指头在摩挲她耳朵背后某个地方。索尼娅已经步入中年,她现在是成年人了,她不再需要人们总是和谐相处,也无法强迫别人这样。他们不太接受她,也不愿对她敞开心扉。比如,凯特就不再接她的电话了。
“可以换另一边了吗?”埃伦问。索尼娅努力点点头。
由于头套在游泳圈里,翻身并不容易,而且得特别小心;某些角度会引发位置性眩晕。让头部保持所谓的看牙姿势很难受。按照埃伦的说法,索尼娅的眩晕是某种精神状况的表现。索尼娅便解释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她的家族中大部分女性都受到了这种精神状况的影响,尽管她不想与外人谈论她的家人。埃伦解析别人的身体时,有某种东西让她想起了大学时上的文本分析课。一切都另有其意,一切都应该升华,要挣脱自身的外壳,上升到某种更高的含义;应该摆脱其原来的意义。仅仅停留在现实还不够。埃伦无法掩饰这种渴望,从她摆在房间各处的许多天使来看,她也不想掩饰。桌子和窗台上都有小天使的身影,连她脖子上戴的项链上也是天使,现在她正走到按摩床的另一边。她想从索尼娅的脚部开始,索尼娅的足弓有点儿畸形。“它们不想抓地。”埃伦曾说。埃伦在她的网站上自称“按摩理疗师”,索尼娅本以为她会用物理疗法,但在埃伦这里,索尼娅的肩膀不是肩膀,而是一种感觉,她的手也不是手,而是她精神状态的表现。作为一名按摩理疗师,埃伦认为解读索尼娅是她的职责,而索尼娅的唯一对策就是解读埃伦。这是一种相互解读的把戏。如果索尼娅的手腕痛,埃伦会说:“也许你把缰绳攥得太紧了。”当索尼娅说,也可能是因为翻译约斯塔·斯文森的小说使她的手在键盘上工作太久了的关系时,埃伦就会说:“那肯定是你的手对约斯塔·斯文森有些抵触情绪。”
这并非完全不可能,但埃伦此刻按摩的不是索尼娅的手,而是她的脚,她的脚伸出了按摩床。凯特的丈夫弗兰克称她为“马赛人”,因为他曾去过非洲,他在那里教非洲人关于风力涡轮机的知识,索尼娅想象他站在大草原的中央。他站在那里,盯着一个马赛人的膝盖骨。他身材矮小,穿着一件T恤,旁边的人高出他不止一个头,而索尼娅也很高,所以他觉得揶揄索尼娅是马赛人很有趣。索尼娅太高了,埃伦不得不把她的小凳子往后挪了几英寸,才能真正够到索尼娅的脚。埃伦擅长按摩,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就身体分析而言,索尼娅的所得超出了她的预期。
“顺便一提,吊坠很漂亮。”索尼娅瞥了一眼埃伦项链上的天使说。
埃伦摆弄着吊坠,说是参加一次研讨会时买的。
她没有接着往下说,不过索尼娅早就知道,有些事情——有些额外的情况——埃伦不想多谈。她对超自然的东西情有独钟,索尼娅的朋友莫莉也对这类东西情有独钟。从索尼娅所能记得的时候起,莫莉对地理和宇宙就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分之感。上中学的那些年里,她们制订了各种外出闯荡的计划。不是索尼娅不够勇敢,而是莫莉能把那些想法不断扩展,并用语言描述出来。那是一个对未来充满狂热梦想的年代,因此,1992年的一天,她们坐上了一辆搬家的车。开车的是爸爸,他噘着下唇,索尼娅和莫莉则铁了心要去东部。起初是合租公寓,后来搬到哥本哈根生活,又过了数年,索尼娅发现自己正置身于莫莉家的一个聚会上,莫莉住在赫斯霍尔姆市的北部。当时一位算命师也在场。索尼娅靠在冰箱旁喝着啤酒,而穿咖喱色长袍的算命师喝着水,她能看到索尼娅的未来。尽管爸爸总是提醒索尼娅,对一切迷信的东西都要避而远之,但她还是站在那里,心里想着,这个女人肯定有某种病,而爸爸曾经还告诉过她,对病人置之不顾是一种罪过。因此她任由算命师喋喋不休。回头想想,算命师曾说她会爱情不幸,显然没有说错。她先是邂逅保罗,然后坠入爱河,最后他却选择了一个仍然梳着法式辫子的二十来岁的姑娘,而那次算命的其他内容被她压在心底。否则你该如何活下去?她一边默默地想,一边试图回忆当时的全部情景。但怎么都想不起来。
“这样疼吗?”埃伦问。
是的,很疼,但索尼娅没有对埃伦说,因为她不想自己的脚底板也被人解读。在日德兰半岛时,她也曾遇见一个能看到鬼魂的人。当时她申请了一个驻留翻译的机会,因为一直在家里与约斯塔·斯文森独处感觉太寂寞了。翻译中心位于一座古老的修道院里,她在那儿没住多久,屋檐下就开始传出窸窸窣窣的动静,地板也老吱吱嘎嘎地响,屋里没人时,房门还自动打开了。到了晚上,猫头鹰会从主楼上空飞过,根据这种种迹象,翻译家们——当时人数不少——编造出了一个鬼魂。无数个夜晚在美酒和闲聊中度过,在他们的谈话中,鬼魂又活动起来了。索尼娅也不甘落后,给鬼魂添加了一些约斯塔·斯文森的元素——时髦的山羊胡子,粗花呢夹克,以及吱吱响的鞋子。这对她来说轻而易举,因为她把他所有的犯罪小说都翻译成了丹麦语,还见过他好几次。接下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她遇见一名工作人员,一名女服务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