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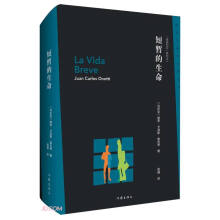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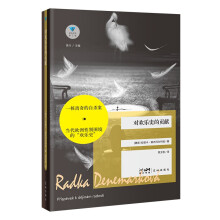




在同年的布克奖短名单上,还有诺奖得主石黑一雄的《我辈孤雏》,而《盲刺客》最终一举夺魁。评委会对这部小说做出了高度评价:“该书视野宽广,结构精彩并富于戏剧性。书中的感情纠葛描写丰富多彩。作者阿特伍德以诗意化的笔触,描写生活细节和人物心理活动。”
桥
大战结束后的第十天,我妹妹劳拉开车坠下了桥。这座桥正在进行维修:她的汽车径直闯过了桥上的“危险”警示牌。汽车掉下一百英尺深的沟壑,冲向新叶繁茂的树顶,接着起火燃烧,滚到了沟底的浅溪中。桥身的大块碎片落在了汽车上。她被烧得只剩焦黑的碎块。
这起车祸是一名警察通知我的:警方查了汽车牌照,知道我是车主。这位警察说话的语气不无恭敬,无疑是因为认出了理查德的名字。他说,汽车的轮胎可能卡在了电车轨道上,也可能是刹车出了毛病。不过,他觉得有责任告诉我:当时有两名目击证人——一名退休律师和一名银行出纳,都相当可靠。他们声称目睹了事故的全过程。他们说,劳拉故意猛地转弯,一下子冲下了桥,就像从人行道上走下来那么简单。他们注意到她的双手握着方向盘,因为她戴的白手套十分显眼。
我认为,并不是刹车出了毛病。她有她自己的原因。她的原因同别人的不一样。她在这件事上完全是义无反顾。
“你们是想找个人去认尸吧,”我说,“我会尽快赶去的。”我能听出自己声音中的镇定,仿佛是从远处听到的声音。事实上,我是相当艰难地说出这句话的;我的嘴已经麻木了,我的整张脸也因为痛苦而变得僵硬起来。我觉得自己好像刚看过牙医似的。我对劳拉干的这件傻事以及警察的暗示感到怒不可遏。一股热风吹着我的脑袋,我的一绺绺头发飘旋起来,就像墨汁溅在了水里。
“恐怕要进行一次验尸,格里芬夫人。”他说道。
“那是自然,”我说,“不过,这是一次事故。我妹妹的驾驶技术本来就不好。”
我可以想象出劳拉那光洁的鹅蛋脸、她那扎得整整齐齐的发髻,以及那天她穿的衣服——一件小圆领的连衫裙。裙子的颜色是冷色调的:海军蓝,或青灰色,或者是医院走廊墙壁的那种绿色。那是悔罪者衣着的颜色——与其说是她自己选择了这样的颜色,倒不如说是她被关在这种颜色里。还有她那一本正经的似笑非笑、她那被逗乐的扬眉,似乎她在欣赏美景。
白色手套是彼拉多彼拉多:古罗马犹太巡抚,曾主持对耶稣的审判,并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在法庭上断案时戴的。她在断绝与我的关系,断绝与我们大家的关系。
当她的汽车滑下桥、坠落沟底之前的一刹那,像一只闪光的蜻蜓悬在午后的阳光中,她想到了什么呢?想到了亚历克斯,想到了理查德,想到了别人的欺诈行为,想到了我们的父亲和他的毁灭?也许想到了上帝,想到了她那致命的三方交易?还是想到了她那天早上藏在五斗橱抽屉里的廉价的练习本?(这个抽屉是我放袜子的,她知道我以后会发现这些本子。)
警察离开以后,我上楼去换衣服。要去停尸所,我得戴上手套和一顶带面纱的帽子。我得有东西遮住眼睛,因为可能会碰上记者。我得叫一辆出租车。而且,我还应该把消息告知正在办公室里的理查德;他一定愿意准备一份讣告。我走进更衣室:我需要穿一套黑色的丧服,再带上一块手帕。
我打开抽屉,看见了那些练习本。它们用粗绳扎成一捆,于是我解开了绳子。我感到自己的牙齿打颤,浑身发冷。我断定自己一定是中风了。
当时我想起的是瑞妮,想起我们小时候跟她在一起的情景。当我们有点擦伤或割伤,就是瑞妮来为我们包扎伤口。母亲也许在休息,或者在别的地方做善事,而瑞妮总是在我们身边。她会把我们抱起来,让我们坐在那张白色釉面的厨房长桌上,旁边就是她正在擀的馅饼面团,或者是正在切剁的鸡,或者是正在剖肚的鱼。她会给我们一块红糖吃,令我们闭上嘴。告诉我哪儿疼,她会说,别嚎了。安静下来,让我看哪儿伤着了。
然而,有些人说不准是哪儿疼。他们安静不下来。他们无法不嚎。
《多伦多星报》(1945年5月26日)
本市死亡事故引起质疑
《星报》独家报道上周圣克莱尔大街发生事故,死亡一人,验尸结果为意外死亡。劳拉•蔡斯小姐,二十五岁,五月十八日下午驾车西行;她的汽车行至桥上突然转弯,冲过桥上维修点的隔离栏,坠入桥下的沟壑,并起火燃烧。蔡斯小姐当场死亡。她的姐姐、著名企业家理查德•E.格里芬的妻子,证实蔡斯小姐患有严重的头痛病,影响了她的视力。对于警方提出的疑问,格里芬夫人否定了蔡斯小姐酒后驾车的可能性,因为后者从不饮酒。
警方认为,汽车轮胎卡在裸露的电车轨道上也是事故的原因之一。人们对市政府有关部门在桥上采取的安全措施是否得当提出了质疑,但经市政工程师戈登•珀金斯证实,安全措施并无不妥。
此次事故再度引起人们对该路段上电车轨道状况的不满情绪。赫布•T.乔利夫先生代表当地纳税人对《星报》记者说,由于电车轨道的管理不善而造成不幸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市政会应当加以重视。
《盲刺客》(劳拉•蔡斯著)
纽约莱因戈尔德杰恩斯莫罗出版社1947年出版
引子: 石园花草谱
她有一张他的照片。她把照片塞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信封外面写着剪报的字样。她又把信封夹在《石园花草谱》的书页中间,料定没有人会去翻看。
她仔细地保存着这张照片,因为这几乎是她留下的唯一与他有关的东西。这是一张黑白照片,是战前用一种笨重的箱形闪光照相机拍摄的;这种照相机的口上带有手风琴一般的皱褶,外面套着做工精良的皮套,看上去像牲口的口套,还配有背带和精细的搭扣。照片是他们两个人一起照的——她和他在一次野餐会上的合影。照片背面有铅笔写的野餐的字样——没有他或她的名字,只有野餐两个字。她心里知道名字就行了,不需要写下来。
他们俩坐在一棵树下。那也许是棵苹果树;她当时没太注意是什么树。她身穿一件白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下面是条白裙子,撩到膝盖。当时一定有一阵微风,因为裙子向上翻卷,贴着她的身体;或者并没有风,裙子就是紧贴身体;也许天气很热。天气确实很热。她把手伸到照片上方,现在仍能感到热气迎面扑来,就像被太阳晒了一天的石头夜半散发的热气。
照片上的那个男人戴着一顶浅色的礼帽,前檐往下倾,半遮着脸。他的脸看上去晒得比她黑。她半对着他,面带笑容;她记不得从此以后她还对谁那样笑过。她在照片中显得十分年轻,太年轻了;当时她并不认为自己太年轻了。他也在微笑,满口的牙齿像点燃的火柴一般闪着白光。然而,他抬起一只手,仿佛要戏谑地挡开她;仿佛要避开将来可能会看他的那些人,避开可能会从这张小小光纸的方框里看他的那些人。他仿佛要避开她,又仿佛要保护她似的。在他那只伸出来的欲挡镜头的手中夹着一个烟蒂。
在没有人的时候,她会拿出那个牛皮纸信封,把照片从一叠剪报中抽出来。她把照片平放在桌子上,然后盯着它看,就像在往一口水井或一个池塘里看——不是在找自己的倒影,而是在找别的东西,一种她丢失的东西;这东西虽然够不着,却还清晰可见,像沙滩上的一颗宝石闪闪发光。她仔细观看每一个细微之处:他那被闪光灯或太阳的强光照得发白的手指;他衣服上的皱褶;树上的叶子,以及挂在枝头的圆圆的小果实——这些究竟是不是苹果?还有前院里的那些粗草。草当时已经枯黄,因为天气干燥。
在照片的一边,还有一只手——你一开始不会发现——腕部以上被框边截去了;这只手放在草地上,似乎被丢弃了,由它自生自灭。
照片上,晴朗的天空中飘浮着被风吹散的云彩留下的痕迹,像冰淇凌抹在了蓝色的金属上。还有他那被香烟熏黑的手指。远处是闪光的河水。如今,一切都被时光的长河淹没了。
这一切虽说淹没了,但还在我的记忆中闪耀。
第一章
桥001
《多伦多星报》(1945)003
引子: 石园花草谱004
第二章
煮鸡蛋007
《环球邮报》(1947)012
公园长椅013
《多伦多星报》(1975)017
地毯018
《环球邮报》(1998)022
口红画的心023
《亨利·帕克曼上校中学之家暨校友会简报》(1998)
030
第三章
颁奖仪式032
银色盒子040
钮扣厂047
阿维隆庄园055
嫁妆066
留声机075
做面包的日子084
黑丝带097
苏打水101
第四章
咖啡馆107
《提康德罗加港先驱旗报》(1933)111
雪尼尔毯子112
《帝国邮报》(1934)117
信使118
《帝国邮报》(1934)125
夜之奔马126
《梅费尔》(1935)130
铜钟131
第五章
裘皮大衣136
疲惫的士兵146
暴力小姐155
奥维德的《变形记》165
钮扣厂野餐会175
布施者187
照片着色200
冷窖211
阁楼223
帝国餐厅232
田园俱乐部240
探戈251
第六章
犬牙纹套裙259
红锦缎263
《多伦多星报》(1935)269
街头漫步270
看门人277
《梅费尔》(1936)285
冰封的外星人286
第七章
扁行李箱295
火窖302
寄自欧洲的明信片312
蛋壳色的帽子324
迷醉330
向阳游乐园338
忽必烈行宫346
第八章
杀戮者的故事357
《梅费尔》(1936)366
Aa’A星球上的桃子女人367
《帝国邮报》(1936)376
大礼帽烤肉馆377
第九章
洗衣服382
烟灰缸390
头上冒火的人399
水妖号406
栗子树416
第十章
西诺星球的蜥蜴人419
《梅费尔》(1937)423
贝拉维斯塔诊所的来信424
高楼426
《环球邮报》(1937)429
联邦车站430
第十一章
洗手间434
小猫438
美丽的景色446
明月当空451
贝蒂小吃店459
便条468
第十二章
《环球邮报》(1938)473
《梅费尔》(1939)474
怒气厅475
黄色窗帘481
电报484
萨基诺城的毁灭486
第十三章
手套489
家中的炉火494
黛安娜甜点店499
悬崖509
第十四章
金色发束515
胜利昙花一现520
一堆瓦砾529
第十五章
尾声:另一只手536
《提康德罗加港先驱旗报》(1999)537
门槛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