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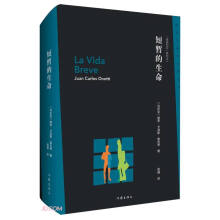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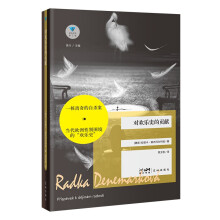




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作家
《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作家
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都不会被记录下来。它将从只有70秒的记忆中消失。
第一章
失忆症笔记:E. H.项目 (1965-1996)
她遇见他,她爱上他。他忘了她。
她遇见他,她爱上他。他忘了她。
她遇见他,她爱上他。他忘了她。
终于,在他们初次见面三十一年后,她和他说再见。临死之前,他彻底忘了她。
他站在低洼沼泽地的木板桥上,两腿微分,脚后跟用力蹬地,以抵御突如其来的狂风。
他站在木板桥上,周围风景秀丽,却十分陌生。他知道自己必须站稳,他用双手抓住桥栏杆,紧紧地。
站在这个陌生、风景秀丽的地方,他却不敢转身去看:在他身后,桥下浅浅的溪水中,躺着溺亡的小女孩。
……全身一丝不挂,大约11岁,尚未发育。两眼圆睁,空洞无神,在水中泛着光。水波晃动,看上去像小女孩的脸庞在抖动。小女孩浑身发白,身材瘦长,两条腿在水中颤动,光着双脚。阳光斑驳,水黾的影子放大了数倍,投落在女孩的脸上。
她不会告诉任何人:“临终前,他不记得我是谁。”
她不会告诉任何人:“临终前,他没有认出我,但他跟我打招呼时,却有着一贯的热切,仿佛我是唯一能给他带来希望的人——‘哈-罗?’”
她会勇敢地向外界承认——E. H.是我的生命。失去E. H.,我的生活将毫无意义。
如果没有E. H.,我不可能取得这些科学成就,也就不可能受邀来此接受嘉奖。
作为一名科学家,一名女性,我所说的都是事实。
她情绪亢奋,说得上句不接下句。她似乎喘不上气来,把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放在一边,望着观众席,眼睛湿润——灯光刺着眼睛,她什么都看不见,神情迷茫,不停眨着眼。观众席模糊成一片,她似乎在人群中看到了他的脸。
我以他的名义,接受这份荣誉。谨以此纪念伊莱休·霍布斯。
这位年度美国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的演讲终于结束了,听众们悬着的一颗心也随之放下来,大家长舒一口气。掌声急促、短暂,散落在偌大的圆形会场里,好像微风中猎猎飘动的小旗子。随后,获奖人转身离开领奖台,神情茫然、不知所措,像是出于同情,掌声开始汇聚起来,一浪高过一浪,如雷贯耳。
她受到惊骇。有一瞬间,她骇怕极了。
他们在嘲笑她吗?他们——什么都知道了吗?
她跌跌撞撞地走下领奖台,忘记拿走上面刻着她名字的奖杯。那是一座18英寸金字塔形状的切割水晶奖杯,十分笨重。很快,一位年轻人过来帮她拿起奖杯,扶住她。
“夏普教授,小心台阶!”
“哈-罗?”
怪事一:伊莱休·霍布斯与玛戈特·夏普打招呼时,格外热情,仿佛很多年前就认识她。仿佛他们之间感情深厚。
怪事二:伊莱休·霍布斯跟玛戈特·夏普想象得完全不一样。
1965年10月17日上午9点07分。玛戈特·夏普迎来她生命中*重要的拐点,也是她职业生涯的重要拐点。
非常巧合,第二天就是玛戈特·夏普的24岁生日——(在宾夕法尼亚州达文公园没有人知道。玛戈特刚刚从美国中西部过来,这里没有谁认识她)——米尔顿·费瑞斯教授向失忆症患者伊莱休·霍布斯介绍时,说她是费瑞斯神经心理学实验室的一名学生。玛戈特是著名“记忆”实验室*新、*年轻的成员。她在众多申请者中脱颖而出,被费瑞斯录取为研究生一年级学生,想到即将开启的生活,她十分紧张。一连好几个星期,她都在阅读跟E. H.项目有关的材料。
然而,失忆症患者E. H.非常友好,也非常绅士。玛戈特立刻感觉没那么紧张了。
E. H.个头特别高——至少六英尺二英寸(约188厘米)。他身姿挺拔,充满活力。皮肤散发出健康的光泽,眼睛看起来与常人无异(玛戈特知道他左眼视力很差)。他跟玛戈特预想的病人完全不同。15个月前(当时他三十七岁),E. H.大脑遭受到毁灭性的创伤,不得不重新开始学习一些*基本的身体技能。
玛戈特觉得E. H.身上散发着一种超凡的男性魅力——一种让人不由自主受到吸引的神秘气质。他衣着考究,有常青藤学院风:干净的卡其裤、长袖亚麻衬衫、牛血色软帮皮鞋露着花纹棉袜。他跟玛戈特见过的研究所其他患者形成强烈对比。那些患者通常穿着病号服或皱巴巴的便服闲荡。玛戈特听说,E. H.是费城显赫世家霍布斯家族的后代。霍布斯家族是贵格会[贵格会(Quaker),又称“教友派”(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成立于17世纪的英国。贵格会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主张和平主义和宗教自由,现在主要聚居地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教徒,美国内战前“地下铁路”[“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way),所谓的地下铁路,实际上并不真的在地下,也不完全是铁路,而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它是十九世纪南方黑奴在同情者和废奴主义者的帮助下,由南方的蓄奴州向北方的自由州逃离的一系列道路网络的统称,其方式包括了铁路、公路和水路。]组织的核心力量。E. H.在当地有很多亲友,但没有妻子、孩子和父母。
玛戈特还听说,伊莱休·霍布斯很有艺术天分。他有一个素描本,还有一个笔记本。患病之前,他在费城的家族投资公司担任合伙人,再之前,他在纽约协和神学院读书,是民权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与追随者。伊莱休·霍布斯年近40,却仍孑然一身,这一点很令人费解。玛戈特觉得,或许这位有着贵族气质的男人发现交往的女性只是爱慕他的钱财,于是就断然分手了——他可能从未料到,恋爱、婚姻和为人父的机会竟然这样仓促画上了句号。
去年夏天,E. H.独自去纽约州东北部乔治湖[ 乔治湖(Lake George),位于阿第伦达克(Adirondack)山脚,为普罗斯佩克特山和布拉克山等低山环绕,自乔治湖村向北延至泰孔德罗加(Ticonderoga),以景色宜人闻名。]的一个小岛上露营,感染了一种毒性特别强的单纯疱疹病毒,该病通常表现为口唇疱疹,会在数天内消退;在E. H.的病例中,病毒感染沿着他的视神经传播到大脑,导致长时间高烧,继而严重损害了他的记忆。
*糟糕的是,E. H.寻求救护之前耽搁的时间太久。他像一位好奇心强到病态程度的科学家一样,用铅笔在笔记本上记录自己的体温变化(*高体温103.1华氏度[ 103.1华氏度,约为39.5摄氏度。])——一直记录到他昏迷过去。
这真是太讽刺了:一种勇武的自我毁灭。像极了英年早逝的画家乔治·贝洛斯[ 乔治·贝洛斯(George Bellows, 1882-1925),美国现实主义画家,以对纽约城市生活的大胆描绘而闻名,是“垃圾箱画派”(Ashcan School)主要发起人之一。]。贝洛斯患染阑尾炎,却不愿意离开画室寻求救护,*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广袤的阿第伦达克地区,没有一流的医院,也没有足够的设备治疗这种罕见的危重感染。救护车将这位神志不清、浑身抽搐的患者送到奥尔巴尼医疗中心,为他施行急诊手术以消除脑部水肿。然而,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他大脑中一些重要的东西已经遭到破坏,损伤似乎不可逆转。(E. H.米尔顿·费瑞斯教授猜测,受损区域是被称作海马体的小型海马状结构,位于脑干正上方,与大脑皮层相连。人们对该区域所知甚少,但它似乎对人类记忆的整合与存储具有非凡的作用。)因此,E. H.无法形成新的记忆,对过去的记忆变得十分模糊。用临床术语来说,E. H.患上了部分逆行性遗忘症和完全顺行性遗忘症。尽管E. H.在国际标准智商测试中得分依然很高,尽管他的外表和举止看起来都很正常,但E. H.“记住”新信息的时间*多不超过70秒;通常情况下不足70秒。
70秒!简直是一场噩梦!
玛戈特觉得,唯一令人欣慰的是,E. H.为人十分友善,似乎也很喜欢得到陌生人的关注。至少他不会遭受精神层面的痛苦——(玛戈特这么认为)。他对遥远过去的记忆有时候生动细致,充满梦幻色彩,而对稍近时期(患病前18个月左右)的记忆则模糊不清。这两种情况都属于“轻度解离性(分离性)”——似乎属于另一个人,不应该发生在E. H.身上。患者很容易受到情绪影响,不过情绪范围十分有限;患者的情绪已经扁平化,就好像漫画是人类复杂性格的扁平化写照一样。
(不可思议的是,E. H.总是选用同样的词汇,用同样的方式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然而,他从来都不确定自己的记忆是否准确,即使外部证据显示他记忆正确,他自己也无法确定。)
虽然E. H.并不总是能够记得他的某些亲人(亲人们的面容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改变),却能够认出照片中的名人面孔(在他生病之前的那些名人)。有时,他会在背诵方面表现出非凡的、天才般的记忆力:统计数据、历史日期、歌词、连环画人物对话和电影对白(据说他能背出默片《战舰波将金号》[ 《战舰波将金号》(Potemkin)系1925年苏联电影艺术大师爱森斯坦执导的默片,受到各国人民和各国电影艺术家电影理论家的交口称赞,世称默片时代的巅峰之作。]的全部内容),在学校读书时背诵过的诗歌段落(惠特曼诗篇《当紫丁香*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是他的*爱)以及美国著名演讲(亚伯拉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和《论四大自由》、小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他痴迷“新闻”——观看电视新闻,每天必读《纽约时报》和《费城询问报》——却什么也记不住。他每天都会做《纽约时报》的填字游戏,然而(他的家人证实)他患病前只是偶尔花时间做这个游戏。(“伊莱可耗费不起那个时间。”)
E. H.似乎能够不假思索地背诵乘法表;能够心算解决代数问题,完成一长串数字的加法。因此,伊莱休·霍布斯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商界脱颖而出,也就不足为奇。
玛戈特觉得,人们很难对一位外表看上去健康的人产生像对(身体)残疾人的那种由衷的怜悯,毕竟他看起来没什么大碍。事实上,虽然E. H.被一再告知自己患有严重的神经功能缺损,他自己似乎也没有觉得这个病有多严重——比如,为什么患病后,他就得随身带个笔记本。
玛戈特·夏普自己也准备了一个笔记本,记录一些准私人文档:主要关于科学研究,也会有部分私人日记或日志。从参加米尔顿·费瑞斯的记忆实验室开始,她就有了这个想法。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她将从笔记本(肯定会有很多本)中提取资料,撰写科研论文或学术专著。记录在很多笔记本上的“失忆症笔记:E. H.项目”将会被转录成计算机文件,一直记录到E. H.去世(1996年11月26日),还会跟踪记下失忆症患者去世后大脑被从头骨中小心翼翼取出。
1965年10月的这天早上,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达文公园的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里,玛戈特·夏普的科学家生涯拉开帷幕。被介绍给E. H.时,她紧张地浑身颤抖,就像被人带到悬崖绝壁旁望着令人眩晕的景色。
我的生命终于要开始了吗?我的真实人生。
我们知道,科学领域存在着超大物质和微小物质
人生也是如此。
一个尚未被普遍认可、尚未被公开承认的事实是:我们都会过真实的人生,也会过苟且的人生。
或许有的人毕生都过不上所谓的真实人生。或许,通常情况下,多数人都只是苟且度过一生。对社会或后代而言,苟且的人生几乎毫无意义。
然而,这并不是说,苟且的人生就等同于琐碎的生活。苟且的生活也可能愉快而有成就感:我们都希望爱和被爱,跟家人和一小圈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无比开心。但这样的人生终结时,稍大一点的世界毫无感知。几乎掀不起一点涟漪,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苟且的人生留不下任何记忆。
玛戈特·夏普的家人就过着这样的苟且生活。她的家乡位于密歇根州奥吉布韦县中北部的城乡结合地区,那里的人都过着苟且的生活。然而,玛戈特12岁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不像周围人那样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她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真实生活,只要有可能,她会第一时间离开家乡奥瑞恩瀑布镇,离开她的家人。
奥瑞恩瀑布镇的年轻人也会离开家乡——应征入伍、考进州立大学在各地的分校、入读护理学院,等等。但他们都会重回家乡。玛戈特·夏普知道自己不会再回去。
玛戈特从小就有很强的好奇心,喜欢刨根问底。她人生中*喜欢的第一本书是11岁时在图书馆书架上发现的彩绘版《物种起源》,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进化。她童年时喜欢的另一本书是《“科学女神”居里夫人》。中学时,偶然读到一篇关于伯尔赫斯·斯金纳和“行为主义”的文章,激起了她的浓厚兴趣。她一直在追问那些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玛戈特认为,要成为一名科学家,就应该知道追问哪些问题。
从伟大的达尔文那里,她知道,可见的世界是由结果构成的,而结果则是事实与条件的叠加。要理解这个世界,需要有逆向思维的能力,从结果出发,反推过程。
只有通过逆转时间(姑且认定),才能够获得驾驭时间的能力(姑且这么说)。你将发现自然“法则”并不神秘,而是像贯穿密歇根州南北的75号州际公路出口一样可知可感。
一个人的生活灾难(E. H.的毁灭)却给他人带来了希望与期待(米尔顿·费瑞斯的“记忆”实验室)?让他们拥有事业发展和成功可能性?)这太不公平、太具讽刺意味了吧?
这就是科学之道,玛戈特想。科学家寻找研究被试,就像捕食性动物寻觅猎物一样。
至少,没有谁像纳粹医生那样,为了研究脑炎病毒的可怕后果,将病毒注射到伊莱休·霍布斯的大脑中去;也没有谁为了某种假定的利益对他施行可怕的神经外科手术。黑猩猩、狗、猫和老鼠被大量用作实验对象。20世纪40-50年代,曾一度十分盛行的前额叶切除手术,往往造成灾难性后果(幸亏那些精确的记录)。
有时候,脑叶切除术引起的剧烈变化,至少会被患者家属认为“有好处”。曾经叛逆的青少年突然变得温顺起来。在男女关系上很开放的的青少年(通常指女性)变得被动、温顺,甚至性冷淡。顽固、易怒、暴躁的人变得像孩子一样听话、乖巧。对家庭和社会“有好处”,对患者自身而言,却未必如此。
就伊莱休·霍布斯的病情来看,疾病似乎彻底改变了他的性格,因为没有哪个像他这样身家、地位的男人会那么单纯、那么容易信任他人,那么执拗而天真地满怀希望。在E. H.面前,你会隐隐感到不安,因为他总是那么热切地推销自己——想要讨好。据说,E. H.的变化太大,患病几个月后他的未婚妻就与他解除了婚约;他的家人、亲戚、朋友探访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如今,他住在费城城郊的富人区格拉德温,与一位“富孀”姑母(他先父的妹妹)生活在一起。
从玛戈特本人的经历,她知道,接受身体疾患病人比接受记忆缺失病人容易得多。继续爱患有身体疾病的人比爱患有记忆缺失的病人容易得多。
尽管玛戈特小时候非常爱她的曾祖母,心里却十分排斥家人带她去养老院看望老太太。玛戈特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因此她选择遗忘。
然而,E. H.与患阿尔茨海默病(去世后才诊断出)的曾祖母情况完全不同,若非事先知道E. H.的具体情况,你不会很快清楚他神经缺陷的严重程度。
玛戈特很想知道:E. H.的脑炎是蚊子叮咬引起的吗?是某种特殊种类的蚊子吗?又或者,只是普通蚊子,感染了脑炎病毒的普通蚊子?单纯疱疹性脑炎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传播?纽约州乔治湖以及周边地区,是否还有其他类似感染病例?在阿第伦达克山区呢?她认为,奥尔巴尼医疗中心的研究员应该在调查这个病例。
“太可怕了!可怜的人……”
每个见到E. H.的人,一走到他听不见的地方,准会这么感慨。
至少,玛戈特·夏普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相比玛戈特,实验室其他同事对此已稍适应,毕竟他们与E. H.已经接触了一段时间。
玛戈特紧张地朝这位病人笑笑,可对方却并没有觉得自己生病了。她对他微笑,他回她一个微笑,带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她想: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认识我。他正在从我这里寻找线索。我千万不能给他任何误导性信息。)
玛戈特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场合。她第一次面对一个活的被试。她不由自主地同情E. H.,对他所陷的困境感到恐惧:一位英俊潇洒、精力充沛、健康活力的男人,正值壮年却突遭重创,体重锐减20多磅,白血球数急剧下降,重度贫血,神志失常。像E. H.这样由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导致的脑炎非常罕见,可以说是万不及一。
然而,E. H.却并未表现出一丝戒备、警惕或不礼貌的态度;像一位在自己家待客的主人,只是一时记不起客人的名字罢了。事实上,他在研究所一直都很自在——至少,从未表现过烦躁不安。每当需要接受检查或测验时,都会由一名工作人员开车到费城郊区E. H.的姑母家中,把E. H.接到研究所。E. H.起初在研究所住院治疗,出院后定期来研究所接受门诊护理。尽管E. H.认不出研究所的任何人,但他发现大家都认识他,这一点让他非常开心。
由于丧失了自我反思的能力,他似乎没什么烦恼。他念她名字“玛—歌”[ E.H.将玛戈特(Margot)的名字读作Mar-go,不仅从读音上将原来音调较强的扬扬格变为了较柔和的扬抑格,且Margo的英文名翻译是“珍珠”,适合用作女性的名字,*早来源于波斯语、德语、法语、希腊语、匈牙利语、英语。通常认为叫Margo的人聪明、美丽、有趣、开阔、特别。]的方式让她十分感动——仿佛这是一个美丽而独特的名字,而不是那个总让她感到别扭的扬扬格音节。
尽管米尔顿·费瑞斯只是例行介绍一下这位*年轻的实验室成员,E. H.却郑重其事。他礼貌地握住她的手,轻轻摩挲着。他俯身靠近玛戈特,像是要闻她身上的味道。
“欢迎——‘玛戈特·夏普’。你是——新来的医生?”
“不是,霍布斯先生。我是研究生,费瑞斯教授实验室的研究生。”
E. H.赶紧自动更正,“‘研究生——费瑞斯教授实验室的研究生’。没错,我知道。”
E. H.用热情高昂的调子重复着玛戈特的这句话,似乎那是个需要破解的谜语。
有记忆困难的人,能够通过重复或“默诵”事实或一串句子来克服障碍。但玛戈特不知道E. H.的重复能否帮助他理解,抑或只是机械地重复。
对于脑损伤病人来说,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处都充满需要破解的谜团——自己在哪里?这是个什么地方?周围这些人是谁?在这些困惑之外,还有一个更大、更费解的谜团,那就是在鬼门关走过一遭后,自身的存在和生存问题。(玛戈特觉得)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太过深奥。这位短时记忆十分有限的失忆症患者像极了将脸紧紧贴在镜子上的人,因为太近,压根无法“看见”自己。
玛戈特很好奇,E. H照镜子的时候能够看到什么。镜子里的那张脸是否每次都会令他惊讶?这是谁的脸?
同样令人感动的是——(尽管这可能归因于他的神经缺陷,而非他的绅士风度)——E. H.对这些来访者,无论是*微不足道的(玛戈特·夏普),还是*举足轻重的(米尔顿·费瑞斯)一律无差别对待。他已经失去了划分等级的能力。不知道E. H.如何区分费瑞斯的其他助手,或“同事”(费瑞斯习惯称他们“同事”,虽然他们实则只是“助手”。这些人E. H.之前全都见过。):一位年龄较长的女研究生,几位博士后研究员,还有一位杰出的年轻助理教授,据说是费瑞斯的得意门生,两人已联合署名在神经科学杂志上发表过数篇重量级学术论文。
E. H.迟迟不肯松开玛戈特·夏普的手。紧紧挨在玛戈特身边,好像在偷偷闻她的头发和身体散发的味道。玛戈特很不自在,她不想惹米尔顿·费瑞斯教授不高兴;她知道导师一直在等着开始今天上午的测试。测试在研究所测试室里进行,需要持续好几个小时。然而,E. H.却被这位年轻、可爱的黑发女子深深吸引住了,他完全忘记了这些人来访的目的。
(玛戈特突然想到,脑部受损的人是否可能通过增强嗅觉补偿记忆缺失?玛戈特想,这是一种合理而令人兴奋的可能,将来有机会她要开展研究。)
(这位失忆症被试对玛戈特的兴趣明显大于对其他人——她希望这种兴趣不是单纯的性吸引。她突然又想到,这位被试的性行为是否受失忆问题影响,影响程度如何……)
然而,E. H.跟她讲话时的亲切、和善,完全拿她当成一个小女孩。
“‘玛-歌。’我猜你是我在格拉德温念小学时的同学——‘玛-歌·麦登’——还是‘玛格丽特·麦登’……”
“恐怕不是,霍布斯先生。”
“不是?真的?你确定吗?应该是1930年代末。斯卡拉特老师班上,六年级,你坐在前排,*左边靠窗的位置。你头上总别着银色的发夹。玛吉·麦登。”
玛戈特感觉自己的脸发烫。她非常不自在,倒不是因为E. H.说话时的温情脉脉,而是觉得自己与在场的人共同合谋,向E. H.隐瞒了他的真实情况。
费瑞斯教授应该坦白告诉他;或者,再告诉他一次。(事实上,他们已经告诉E. H.无数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