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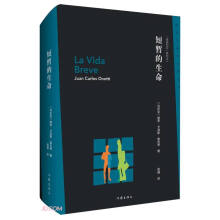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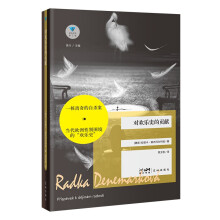




在某些情况下,所谓的下午茶聚会应该是生活中惬意的时光了。有些时候,无论你是否饮茶——当然有些人从不——茶会本身就令人欢愉。在我开始讲述本书简单的故事时,脑海里就浮现出那些场合,为这一单纯的消遣提供美妙的场景。在一幢古老的英国乡间住宅的草坪上,摆放着小小的盛宴所需的桌椅茶具等。时值阳光灿烂的夏日午后,正是为曼妙的时刻。午后的一半已经逝去,却还有许多剩余,而这剩余的部分恰恰美妙绝伦。真正的黄昏几个小时后才会降临,夏日强烈的阳光却已减弱;空气变得柔和,柔软厚密的草坪上阴影缓缓拉长。一切都弥漫着尚未到来的悠闲意味,也许这就是人们在这一时刻,享受这一场合的主要原因。下午五点到八点有时会构筑一段小小的永恒,而在现在的情况下,这段空间只能是欢乐的永恒。此刻,在场的几个人正安静地享受着这段愉悦的时光,却并非一般认为热衷于这一仪式的女性。几个阴影交错笔直地投射在平整的草坪上,它们来自于一位老人和两个年轻人。老人坐在一张宽大的藤椅里,旁边是一张矮桌,下午茶已经摆放妥当,前面是两个年轻人,一边来回踱着步,一边闲聊。老人的茶杯端在手里,形体硕大,色彩鲜艳,和桌上的其他茶具风格迥异。他面朝着房子,把茶杯长时间地端在胸前,小心地啜饮着。两位同伴或者已经喝完了茶,或者并不在意这一享受。他们一边抽着雪茄,一边漫步。其中一个在经过老人时,不时关切地看看他;老人却浑然不觉,眼睛凝视着房子华丽的红色前墙。而耸立在草坪那边的这座建筑也的确值得老人如此专注的观赏。在我试图描述的这幅典型的英国画卷中,它是富有特色的景物。
它坐落在低矮的山坡上,依山望水,下面是泰晤士河,自四十英里外的伦敦逶迤而来。那是一幢尖角建筑,红色的砖墙向两边延伸,岁月的风霜在它的外观上极尽所能,却只是让它更加优雅。呈现在草坪上的是大片的常春藤,簇拥的烟囱,和掩映在爬墙植物后的窗户。这幢房屋年代久远,享有盛名。喝茶的这位老绅士会很乐意地告诉你:它建于爱德华六世时期,曾经恭迎伊丽莎白女王圣驾(她尊贵的身体曾经在一张巨大华丽,坚固笨重的卧床上睡过一夜,这至今仍是卧室的荣耀),克伦威尔战争时期遭到严重损毁,复辟时期加以修缮和扩建,十八世纪时又改建为另一风格,后落到一位精明的美国银行家手里,由他细心保护下来。他起初买下它只是因为价钱诱人(当时的情况及其复杂,不容赘述):可心里很是抱怨它的丑陋,古旧和不便;如今,二十年将要过去了,他却对它产生了一种真正的审美情怀。他熟知它的每一个尖角,而且会告诉你欣赏这些尖角组合的地点和时刻——正值那些形状各异的尖角的阴影,以的角度,柔和地投射在温暖褪色的砖墙上。不仅如此,他还能列举出曾经住在这里的大多数房主和房客,其中还有几位声名显赫,就像我刚刚说的;可是,他在这么讲的时候,会不动声色地让人相信,房屋近的命运并不亚于它辉煌的过去。俯瞰我们现在所说的这块草坪的并非房屋的正面,正门在另一面。这里是私密的空间,宽阔的草皮地毯般铺在平缓的山顶上,好像是室内的华丽装饰的延伸。高大安静的橡树和山毛榉撒下浓密的阴影,就像挂着天鹅绒的窗帘。带坐垫的椅子,色彩鲜艳的坐毯,散放在草坪上的书籍和报刊,把这里布置的仿佛一个房间。河流在稍远的地方,那里地势开始倾斜,而草坪也可以说到了尽头。然而,漫步到河边仍会让人无比惬意。
坐在茶桌前的老人三十年前从美国来,除了行李,还带来了一张典型的美国面孔。不仅如此,他的美国面孔还保存得很完好,如果需要,可以完全自信地将它带回祖国。不过目前,他显然不大可能再迁徙了。他的人生旅途已经接近终点,目前不过是略事歇息,等待着那永久的安眠。老人的脸狭窄光洁,五官分布匀称,神态安详而敏锐。一望而知,这张脸并不富于表情,因此那精明满足的神态就显得更像是个优点,好像在说他人生成功,又好像在说他的成功并没有让他唯我独尊,招人嫉妒,反而像失败一样不让人反感。他当然阅历丰富,可是他瘦长的面颊上漾起的淡淡微笑却天真质朴,让他的眼睛散发出幽默的光芒。老人终把那只大茶杯放到了桌子上,动作缓慢,小心翼翼。他衣着整洁,穿着一身质地很好的黑绒衣服,膝盖上围着一条大围巾,双脚套在厚厚的刺绣拖鞋里。一只漂亮的牧羊犬卧在椅子边的草地上,目光温柔地望着主人的脸,而主人柔和的目光则凝望着那仪态威严的房屋。一只毛发耸起的小猎犬来回奔忙着,不时瞟一眼另外两位绅士。
其中一位绅士大约三十五岁,体态匀称,一张英国面孔就像我刚刚描述的那位老年绅士的脸一样典型,只不过完全是另一种类型。这是一张英俊的面孔,很引人注目,面色清新坦率,脸上的线条笔直而坚定,一双灰色的眼睛充满生气,下巴上浓密的栗色胡须让他的脸显得更加漂亮。他看起来幸运、杰出、不同寻常,散发着经过深厚教养熏陶的快乐气质,会让任何看见他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羡慕他。他穿着带马刺的马靴,好像骑马走了很长的路途。头上是一顶白色帽子,看起来有点大,两只手背在身后,一只漂亮的白色大拳头里攥着一双弄脏了的狗皮手套。
他的同伴则是另一种类型。他踱着步,好像在丈量身边草坪的长度。这人也许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可不会像另外一个那样,让人盲目地渴望处于他的地位。他个子高瘦,体态羸弱;五官很难看,面带病容,却别有一种睿智而迷人的气质。他嘴唇上留着两撇小胡子,脸上还有络腮胡,不过乱蓬蓬的,并不美观。他看起来很聪明,却一副病魔缠身的样子——这当然不会是什么幸福的组合。他穿着棕色的天鹅绒夹克,双手放在口袋里,让人觉得这是习惯性的动作。他的腿不够结实,步履蹒跚,摇摇晃晃。我已经说过,每当他经过坐在藤椅里的老人时,就会看他几眼,这时把这两张脸加以对照,就不难看出,他们是父子二人。终于,父亲接住了儿子的目光,回报给他一个温和的微笑。
“我很好,”他说。
“喝过茶了吗?”
“是的,味道不错。”
“再来点怎么样?”
老人静静地想了想,说,“嗯,还是等等再说吧。”他讲话带着美国口音。
“你冷不冷?”儿子问道。
父亲慢腾腾地揉着腿。“哎,我不知道。要能感觉到才能说啊。”
“也许需要有个人替你感觉。”年轻人笑着说。
“哦,要是有人能永远替我感觉,那就好了!你不能替我感觉吗,沃伯顿勋爵?”
“哦,好的,很愿意,”那位称作沃伯顿勋爵的绅士立刻回答说。“看你的样子,我敢说你现在一定非常舒服。”
“嗯,我想没错,在很多方面都是。”老人看看膝盖上的绿色围巾,用手把它抚平。“事实是,我已经舒服了这么多年了,我想我已经习惯了,都感觉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