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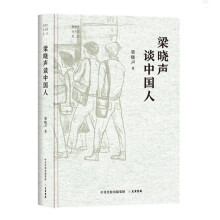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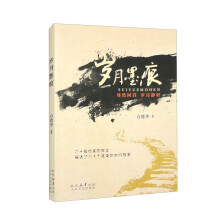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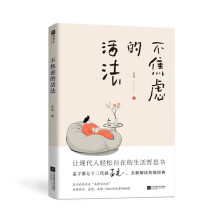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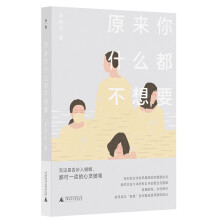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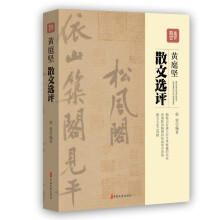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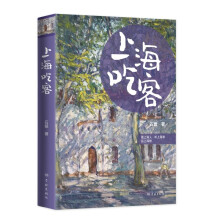

旅行不是为了逃避生活,而是为了不让生活离你而去。
你去过的地方,都会成为你的一部分。
“世界尽头”乌特恰格维克
2017 年 6 月,我乘坐小飞机从阿拉斯加第一大城市安克雷奇出发,前往有着“世界尽头”之称的乌特恰格维克。
乌特恰格维克位于北极圈内,紧邻北冰洋,是全美最北的城市,也是全球最北的城市之一。当地居民以因纽特人为主。大约 1500 年前,他们从西伯利亚越过白令海峡来到这里,定居于此。本以为他们会很快冻死,但他们在北极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此后,这里一直是他们的家园。
乌特恰格维克一度叫巴罗 (Barrow, 1901—2016), 2016 年底才正式改名。我去时机票上仍有巴罗字样。
这是因为那里有个巴罗角(Point Barrow),由英国探险家弗雷德里克 · 威廉 · 比奇在 1826 年命名。巴罗角是全美最北点,也是许多北极探险的起点,这里曾是重要的北极飞行基地,附近还建有美国空军雷达站。“巴罗”对非本地居民来说更容易发音,1901 年建立的邮局更是帮助“巴罗”这个名字成为主导,“巴罗”因此沿用了 100 多年。
为什么又要改回来?
公民投票的结果。用当地议员的话说,更名是出于尊重和支持因纽特语(Iñupiaq)的使用,也是去殖民化的一部分。就像因纽特人不喜欢被叫作爱斯基摩人一样,因为 Eskimo在印第安语里是“吃生肉的人”的意思。
我出发前对乌特恰格维克充满了想象,但其实又无从想象,因为当时我对北极圈和北冰洋毫无感性认识。
我看过 2012 年由德鲁 · 巴里摩尔(Drew Barrymore)主演的电影《大奇迹》(Big Miracle),这是极少以乌特恰格维克为故事发生地的电影之一。影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了在巴罗角附近众人拯救被困冰下的鲸鱼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冬天,小镇看上去就是白茫茫的一片,陆地跟北冰洋面傻傻分不清楚,甚至由于飘雪天空都是白色的。印象最深的是全美的记者赶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一下飞机就开始抱怨:“这是什么鬼地方?”而女主持人穿着雪地靴出镜双脚冻得受不了,因为气温是零下 50℃。
说实话,我不敢尝试冬天去这个地方,冷不说,航班还常常会被取消,不确定因素太多。我想夏天去北极会容易一些,但我心里仍然有一百个疑问,夏天去那里是不是仍要穿羽绒服雪地靴?当地会有 Wi-Fi 吗?道路交通怎么样?和因纽特人相处有什么礼数?
当时关于乌特恰格维克的资料信息还非常少,等我抵达那里,一切疑团才解开。这大概就是中国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意义吧。每到过一个地方,你对这个世界就又多一点认识,少一点偏见。
乌特恰格维克最吸引我的自然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殊人文。阿拉斯加已经非常不同于美国本土,我在西雅图转机时,海关官员得知我要去阿拉斯加时,夸张地做了一个发抖的动作,说“so cold”!而乌特恰格维克位于阿拉斯加最北处,自然更冷更荒凉。在安克雷奇,当地人听说我要去乌特恰格维克时大吃一惊,警告我说,那里至少要落后 25 年。
这让我对这个地方更加好奇了。
乌特恰格维克水陆不通,只能坐小飞机前往(确切地说,远洋海运船会在每年夏季运送货物至此,但一年只有一次,因为北冰洋很快就又冻住了,其余时候都要靠空运)。
飞往乌特恰格维克的小飞机很特别—它的前半段没有窗。原来,它一半用来运货,一半用来载人,舱内中间被硬生生隔断,满员也就 72 个位子。只有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家飞这条航线。
飞机去乌特恰格维克通常不会直达。我那架飞机在死马(Deadhorse)停留了 50 分钟,停留期间我不需要下飞机。
死马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它是阿拉斯加北冰洋油田“普拉德霍湾油田”(Prudhoe Bay Oil Field)的起始地。
众所周知,1867 年,俄国以白菜价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近 172 万平方公里——比新疆还大一点——只卖了 720 万美元,差不多一平方公里四美元。估计美国人梦里都会笑醒。
俄国为什么要贱卖?据说是因为输了 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非常担心据守在加拿大的英军会夺取阿拉斯加,进而越过白令海峡,侵犯其亚洲领土,觉得不如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好有个屏障。
美国人当年也没觉得占了便宜。相反,操持这桩买卖的时任国务卿威廉 · 西沃德(William H Seward)还惨遭讥讽和嘲笑。那荒蛮之地要了干吗?当冰箱用吗?直到阿拉斯加发现金矿(杰克 · 伦敦的小说有描绘)、北冰洋发现油田,美国人才欣喜若狂。
今天,普拉德霍湾油田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原油供给之一。从阿拉斯加北部靠北冰洋的死马,到南部瓦尔迪兹(Valdez),一条输油管道贯穿南北。如果你在阿拉斯加自驾旅游,一路都会看到那粗粗的输油管道和时而驶过的油罐车。油输送到瓦尔迪兹,再从那里转运到美国本土。
我之前曾研究了好久,想有没有可能开车到乌特恰格维克,但我发现,进入北极圈只有一条路—道尔顿公路,而且这条路只通到死马,就是为运送石油而建。乌特恰格维克与世隔绝,没有道路连接到阿拉斯加其他地方。死马位于乌特恰格维克以东约 430 公里,同属北坡区(North Slope Borough),来往也只能靠飞。
我后来走了这条叫作道尔顿的公路—它被 BBC 列为全球最危险的公路之一 —但我没开到终点站死马,而是过了育空河进入北极圈后就返程了,一是时间不够,二是这条路太难开也太孤单了。
所以飞机在死马停留我很兴奋,从飞机窗口往下看,死马非常小,那里主要由工人和在附近普拉德霍湾油田作业的公司的设施组成。
我的邻座恰好为 TSA(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工作,是个专业人士,她要去死马工作两周。她告诉我,没人在死马生活,死马只有工作人员。 这一点与乌特恰格维克不同。乌特恰格维克 2020 年统计人口为 4800 多人。想想也挺有意思,乌特恰格维克是北坡区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却遗世独立,而死马没有居民只有油田,倒有道路通往外界。
一个城市就像一座孤岛,陆路不通,又不长任何东西,它到底怎么运作呢?我对乌特恰格维克更添了一分好奇。
飞机终于抵达目的地。乌特恰格维克的机场似乎比死马也大不了多少,机场只有一条跑道。从飞机尾部走下舷梯,人就几乎已经站在了机场出口。尽管做足了思想准备,我走出机场还是吃了一惊,第一感觉是冷,第二感觉是破。整个城市—如果称得上城市的话—看上去破破烂烂的。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啊?!”难怪人们一到这里,很容易发出这样的灵魂拷问。
前言
“世界尽头”乌特恰格维克
“死亡之路”:道尔顿公路
车轮上的国家
我吃,故我在
总统图书馆
亚特兰大与《飘》
耶路撒冷的美与愁
偶遇大明星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