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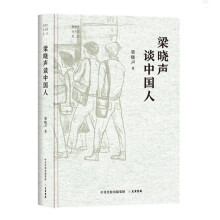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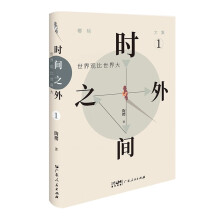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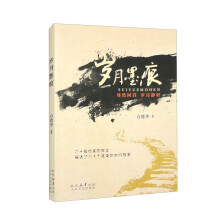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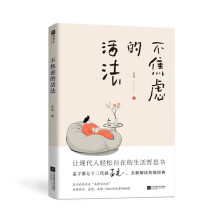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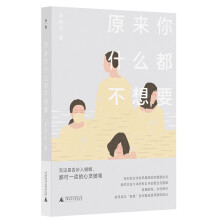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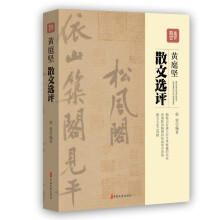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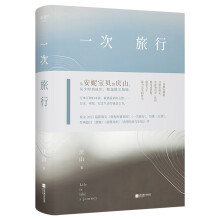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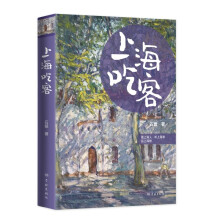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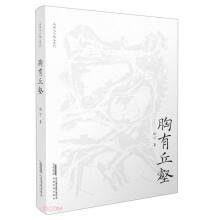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写给年轻人的解惑之书。
本书有对人生的深思,也有对爱、亲情、生活、工作、困顿、孤独的解读与诠释。人生会有许多难,所有不能打败你的,终将使你变得更为强大。
★凡事看淡,才能越活越轻松。
生活在“内卷”时代,学会放下,学会看开,才能找到自在、舒服的生活方式,正如“我们渴望命运的波澜壮阔,经历过才发现,人生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
★是梁晓声的心灵独白,更是梁晓声人生智慧的总结。
本书精选梁晓声温情、哲思、励志散文,写普通人的生活与困惑,从平常中体会作者对人情世事有温度、有深度的思考,领悟生活真谛。
★淡定地守望着自己的生活,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人生境界。
★对于绝大多数的人,人生本就是一堆责任而已。参透此谛,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尤其是缘,不论怎样,皆当润砾成珠。——梁晓声
从复旦到北影(节选)
我到复旦那天,两腿浮肿,鞋袜难脱。以为是在火车上坐的,并不是,是急性肝病的症状。
当天晚上,专业已报到的同学们,聚在一起开“认识会”。天南地北,各自拿出带来的好吃的东西,堆了一桌子。我只剩下几个小苹果,不好意思拿出来,也不好意思光吃别人的,就吸烟。
我的东北老乡,C,女性,放在桌上的是两个哈尔滨特有的“大列巴”,有小脸盆那么大。我只在很小时吃过几次。当时哈尔滨难以买到。大家觉得新奇,切了,你一片他一片,都说好吃,我也拿起一片吃。吃的是老乡的,太客气反而显得疏远。我在一师,C来自五师,原先互不认识。心中暗想,同学中有一个老乡兼兵团战友,真不错。
有一同学问:“听说你们哈尔滨人天天吃这种‘大列巴’?”
C回答:“当然。哈尔滨人个个都是从小吃‘大列巴’长大的!”
我觉得很有纠正一下的必要,便说:“只有百分之五,也许还更少的哈尔滨人是从小吃‘大列巴’长大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从小吃大饼子长大的。”
我说的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当时哈尔滨人的粮食定量是——面粉二斤,大米一斤,其余全是粗粮。米面在一般家庭中,除了过年过节,都是给上班的人带的。
C当即反驳我:“你一个人是吃大饼子长大的,也代表不了哈尔滨人。我就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
我据理力争,说我是百分之九十五中的一个,当然代表大多数哈尔滨人。她不过是百分之五那“一小撮”中的一个,无论如何代表不了哈尔滨人。
她生气了,说:“你说谁是‘一小撮’?告诉你,我的家庭是‘革干家庭’!你侮辱革命干部!”
我说:“我不知道啊!可你为什么要说谎呢?为什么要欺骗这么多初识的同学们呢?你明明知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尔滨人吃的是粗粮!哈尔滨人如果都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哈尔滨人早算进入共产主义了!”
我认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尔滨人究竟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还是吃大饼子长大的,这是非辩论清楚不可的。对于这一类问题,我一向特别敏感,容不得别人当我面说一句假话。
她说:“你的话里明明有对现实不满的意思!”
我火了,说:“咱俩都是工农兵学员,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就算我对现实不满,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她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那我就有权批判你!”
我说:“你不过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共产党员,统计一下,你在共产党员中也不过是百分之五!”
其他的同学就劝解。他们越劝解,我越来气。我希望他们都能够相信我的真话,而不要相信C的假话。但他们似乎对我与C争论的问题一点也不感兴趣,只对“大列巴”感兴趣,这比他们相信了C的话还令我气愤。若在兵团,如果C不是女的,而是男的,说哈尔滨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还坚持,非被吃大饼子长大的哈尔滨青年们合伙揍一顿不可!
怎么能瞪着眼睛认真严肃地说假话呢?
C拍了一下桌子,气势汹汹地说:“你这是在分化我们党员队伍!”
我腾地立了起来,说:“滚你妈的!”将吃剩下那半片“大列巴”,狠狠朝桌上一摔,猛转身离开了,回到自己的宿舍。
我以前从不骂人,是到木材加工厂后学会的。学会了,就觉得在必要时来一句“滚你妈的”,十分管用。
我躺在自己床上,还气得不行,还想再去找C展开一场大辩论。忍而又忍,才忍住怒火。
我的性格中,有种过于认真而又过于激烈的劣根性。在连队,跟几任连干部大吵过。在团里,跟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参谋长大吵过。到木材加工厂,性格依然不改。
我在初二便已入团。到了北大荒,要求重新入团。劳动很能干,不怕苦不怕累的。就是因为这种性格,重新入团竟入不了。四年后,调到团宣传股的前一年,只好又请求恢复团籍,补了十二元多的团费。教训可谓深刻,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现在回想起来,哈尔滨人究竟是从小吃“大列巴”还是吃大饼子长大的,有什么值得辩论的呢?吃大饼子长大的有之,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也有之。干吗脸红脖子粗地争谁代表百分之九十五的哈尔滨人呢?
听隔壁宿舍阵阵说笑声,我忽然意识到,我是换到了另一种环境里。复旦与北大荒太不一样了。我将与之共处的同学也与木材加工厂抬木头的伙伴们太不一样了。我必须正视这个现实。想起陈老师在我们团招待所里对我说过的那番告诫的话,倏然地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孤独感。
隔壁宿舍里不断传来欢声笑语,C的说笑声尤为响亮。同学们吃着她的“大列巴”,当然不会表示怀疑她的话而相信我的话了。
可我从来没有像那时那刻一样,希望自己的话被相信。每月二斤面粉的哈尔滨人——我心里真是有些难过。
隔了两天,我到医务室去看身体复检结果。医生问过我的姓名,翻到我的化验单,只看了一眼,就低声叫道:“乖乖,好家伙!”接着说:“你跟我来,你跟我来!”不用手扯我,用夹化验单的夹板从背后顶着我往前走。我就这么被顶上了医务室的二楼,顶进了一扇三夹板临时做成的门内。我糊里糊涂地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医生说:“肝炎隔离室。”
我这才知道,我是一个带病毒者——转氨酶五百八十以上。
我请求道:“那也得让我回宿舍一次呀!”
医生说:“不行。你的一切东西都得经过严格消毒。消毒后日常用的我们会替你送来。从现在起你不能离开这里!”
共有二十几名各系各专业的新生被关闭在“肝炎隔离室”。我是其中肝指数最高的。大家的活动区仅限各房间,每房间四五人,有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大阳台。阳台下是篮球场。可谁也不愿出现在阳台上,那好像等于自我展览。
我苦闷起来,唯恐被退回兵团。未入复旦,不知复旦名气。入了复旦,方知复旦果果真真是可以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地方。有一个上海“老高三”的新生,与我对面床,每天向我讲复旦的历史。我才知道复旦是出名人的地方,不禁从此对这所大学肃然起敬。
有一天,学校里的气氛似乎显得有些异常。那“老高三”经常偷偷溜出隔离室,带回一些消息。那天他又溜出去了,回来后告诉我们,是某国元首到学校参观,还说翻译就是复旦上一届分配到外交部的学生。“肝友”中一个外语系的,不知为什么就哭了。大家问他哭什么,他说:“我的名额将来是要分到外交部去的,现在却被关在这儿!”大家寂然。
大学既是往人头脑里灌输学问的地方,也是在人头脑里编织梦幻的地方。天天批“智育第一”,学问贬值。“戴帽分配”——即入学前便已预知分配去向,尤使梦幻迷人。想想看,昨天还在握锄把或抡大锤,明天突然进了某某名牌大学,三年后将要被分配到什么外交部、文化部、中宣部、《人民日报》社等好去处,怎地不使人天天做梦呢?
“肝友”中还有一个国际政治系的,是广西农村学员。“老高三”半真半假地对他说,他们这一届国际政治系中,有分配到中国驻联合国办事处去的。他便天天梦想着有朝一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每天不断地冲葡萄糖水喝,以为转氨酶会早降下来。还买了一本《肝脏病知识》,手不释卷。一会儿用小镜照舌苔,一会儿看手,害怕发现“肝掌”。
我也借来那本《肝脏病知识》读,也学会了长长地伸出舌头照着小镜自己观察自己的舌苔,也学会了观察身上有没有“蜘蛛痣”,手上出没出现肝掌。也梦想,梦想有朝一日分配到黑龙江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做一名编辑。为这个梦想也暗暗祈祷过,不是祈祷上帝,而是祈祷“复方”什么“草冲剂”——医生每天给我三次的草药汤。
一天,刚刚吃过晚饭,正躺在床上忧愁,忽听外面有人喊我。走到阳台上,朝下一望,是陈老师。见了他,就如同见了一位久别的亲人,不禁泪潸潸无语。他仰视,我俯视,我俩好像戏台上《空城计》中的诸葛亮和司马懿。他见我那可怜样子,安慰道:“别想得太多,安心养病。思想负担太重,对肝病也是不利的。”
我说:“我真怕被退回去。”
他说:“一般情况下不会的。肝炎没那么可怕,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
陈老师走后,我回到隔离病房,重新躺在床上,感到内心的忧郁稍释。
同学小莫给我送来十几封信。一封家信,其余全是木材加工厂抬大木的伙伴和宣传股的朋友们写来的。信给我带来了一些安慰。
有三封信是宣传股的姑娘们分别写来的。我们宣传股只有三位姑娘。北京姑娘小徐是广播员,天津姑娘小张和鹤岗姑娘小张都是放映员。我总是叫她们“张天”“张鹤”。我们宣传股在政治部人最多,加上三名报道员、三名干事、两名男放映员,可谓是一个大家庭。股长当年也才三十六七岁,现役军人,是我们的“家长”,令我们感到很可亲的一位“家长”,在我们面前,半点也没有股长的架子,对政治部主任也是“敬而远之”。
我们宣传股的知青之间非常友好。三位姑娘,像我们的三位妹妹一样。这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时似乎谁也没有谈情说爱的念头,关系都很单纯。起码我自己那时没有产生过与三位姑娘中的哪一个谈情说爱的念头,也从未看出其他几个小伙子对三位姑娘有过这种表示。
我上大学两年之后,我在宣传股时那种互相之间友好的关系就分崩离析了。都是爱情把这种关系搞坏了。毕竟不是亲兄妹们。到了年龄,小伙子们总希望某一个姑娘不再是自己的“知青姊妹”,而成为自己的妻子。这是任谁也没办法阻止的。只有互相不被吸引的青年男女之间才有所谓纯粹的友谊。这是一条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定律。伪君子们才企图证明这条定律是错误的。
第一章 忆当年
第一支钢笔
我的少年时代
兄长
我的父母•我的小学•我的中学
小街啊小街
第二章 心安处
从复旦到北影
五角场•阳春面•蜡像馆
回首忆年
父亲的遗物
第三章 血犹燃
几个春节一段人生
我的梦想
一种愿望,一种理想
我的中国梦
我们的下一代真是“小上帝”吗?
用我们的热血喷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