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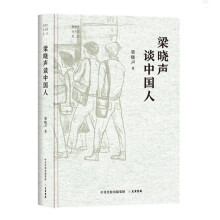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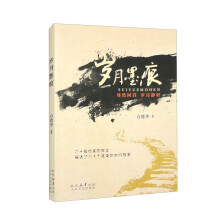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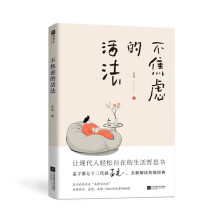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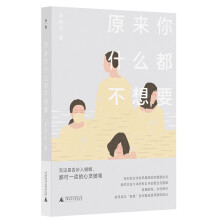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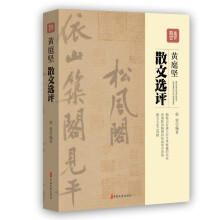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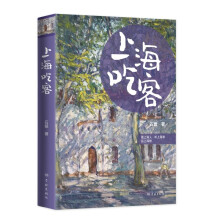

从土高中到复习班
——我的三次高考
大概是 1976 年的某一天,我父亲特意从公社回家,拽上我去城里电影院看了一部《决裂》的彩色故事片。这部影片不打仗,我看得并不来劲,却也小有收获。“马尾巴的功能”很搞笑,我像所有的观众那样,也在电影院里笑得一塌糊涂。龙校长举起一位考生的手,说这手上的硬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我立刻意识到硬茧的重要性,伸开自己那双小手瞧一瞧,细皮嫩肉的,我就有些灰心。什么时候我这双手才能长成、练成电影里那双青筋暴突、骨节粗壮、老茧深厚的手啊。
很可能这就是我对大学的最初认知,它不是北大、清华,也不是牛津、哈佛,而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一年之后,高考恢复了,《决裂》成为一出荒诞剧。我也正 是在这一年上了高中。高中原本办在我们村里,但不知什么原因,一年之后却被合并到水东中学。水东是人民公社的所在地,把设在大队里的高中关停似乎也理所当然,但在我看来,水东中学与我原来就读的水北五七学校并无多大区别。因为两个学校都安顿在稍事修葺的庙院里,我们的转学似乎也就成了小和尚的迁徙。只是要走到水东那个庙院花费的时间稍长,它在三里路开外。
教我们的一些老师也调入水东。比如牛春德老师,他曾是我父亲的数学老师,我上高中时他又开始教我们历史。但一校之长张永祥老师并没有过去,他只是给我们讲过一次或是两次哲学,我还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就远离了讲台,他的哲学课也成为绝响。
我们合并到水东中学时举行过一次快慢班的分班考试,语文题由刘怀仁老师所出。他那种不按常理出牌的考法把许多人都考煳了(比如,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一道题是,默写以“一” 字打头的 20 个成语),但我在这次考试中却大获全胜。刘老师与我父亲私交甚好,他也就不时溜达到公社大院里与我父亲抽着烟袋侃大山。他向我父亲吹牛:“赵勇的语文嘛,班里同学要想赶上他,还得学十年。”当父亲把这个内部消息婉转地告诉我时,我很是得意了一阵。而许多年之后我已明白,那并不是我的语文有多好,而是我的那些同学的水平实在是太差了。或许是刘老师的煽乎让我父亲看到了一线希望,他开始关心我考大学的事情了。
父亲的同事张建民是 1977 年晋城县的理科高考状元,却因为政审不合格而窝在水东公社,父亲就让他给我补习数学。但我天生没有数学头脑,横竖不开窍,白费了他那么多时间。
就是在那所两年制的土高中里,我开始了中学阶段最后一年的学习。那时候我的年龄尚小,对考大学只有一些懵懵懂懂的认识。我大概觉得,能上大学总归是一件好事,但自己能不能考上,却实在是心中无数。而我所在的班级也没有几个认真学习的主,他们还像以往一样调皮捣蛋着。大我一两岁的同学已处在春机发陈的年龄,他们课前、课后与女同学尽情调笑。看到哪两个少男少女有了点意思,他们就会恶搞一把;觉得哪两位比较般配,他们又会拴对儿,诌出顺口溜编排一番。
这时候,他们就成了赵树理笔下的李有才。水北到水东是一条河滩路,路的两边种着杨树,树上总是歪七扭八地刻写着“李有才们”的作品,或者是经过他们拴对儿之后的男女同学的名字。十多年之后,我读到了台湾诗人纪弦的《你的名字》,诗中写道:“刻你的名字!/ 刻你的名字在树上。/ 刻你的名字在不凋的生命树上。/ 当这植物长成参天的古木时……”那时候我就有些恍惚,忽然想起了小时候那排白杨树,莫非纪弦也经历过这种事情?一位年轻的老师教我们英语,他那句“What’s this ?”的水东英语一出口,立刻就被人演绎成“我吃你屎”, 但这么说显然是自取其辱,于是它又立马被改写成“你吃我屎”。课间、课后,大家便沉浸在一片“你吃我屎”的对攻 与笑骂中。结果那一年的高中英语课,我只记住了这么一句。
上编 私人生活
我的学校我的庙——七十年代纪事
我的老师刘怀仁
从土高中到复习班——我的三次高考
青春的沼泽——我与《批评家》的故事
遥想当年读路遥
奶奶的记忆
姑姑老了
故乡一望一心酸——过年散记
下编 秋叶静美
生如夏花之绚烂——忆念业师程继田先生
蓝田日暖玉生烟——忆念导师童庆炳先生
落花无言 人淡如菊——忆念陈传才老师
为谁风露立中宵——我所认识的王富仁先生
弄潮儿向涛头立——我眼中的雷达先生
出来是完全正确的——忆席扬
人生的容量——忆再华
逝者魏填平
后记